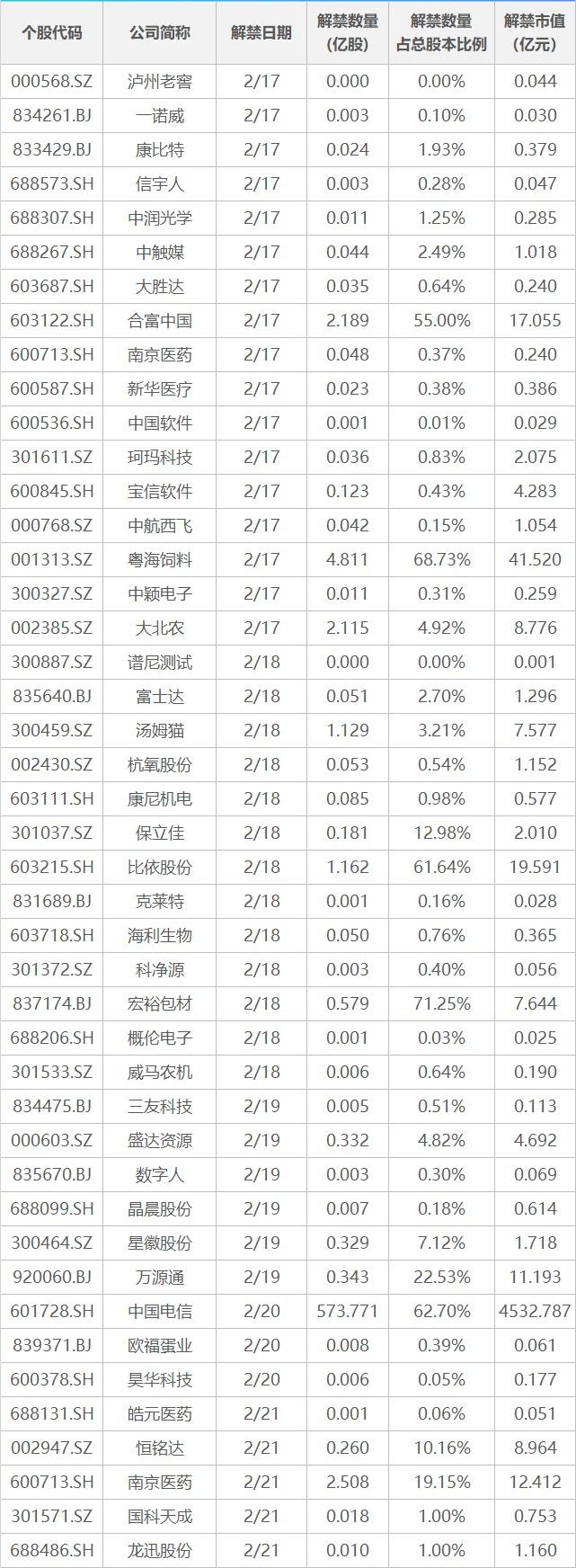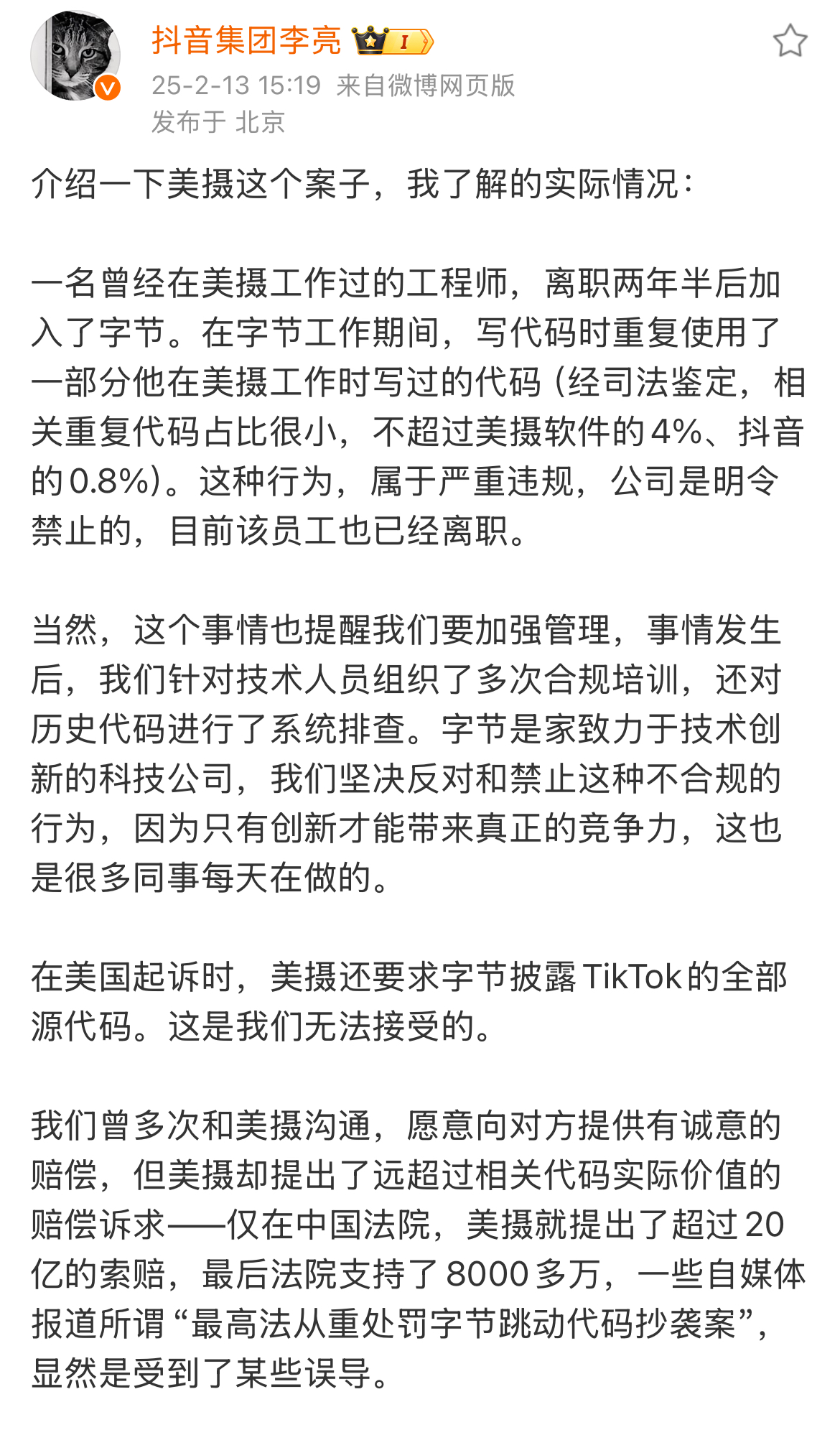他在纽约做“公务员”,预算局分析师“像是侦探”
一个好的城市能让游客流连忘返,也能让这里的居民和管理者脸上有光。但怎样让一座城市变得更好,却是整体上很神秘、细节上很费功夫的大工程。
特别是近年,中国城市走出了彼此竞争的“排行榜”时代,又不由自主地进入被社交媒体审视、评判和比较的新赛道中。在城市更新广泛实施的当下,人们喜欢上一个城市往往有具体的舒适感受和难忘回忆。有时,一次在新改造开放的网红地标打卡的美好经历,就胜过耗费巨资所做的城市形象宣传。这说明,精细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力量。
在新书《创造大都会:纽约空间与制度观察》中,城市研究者、规划师罗雨翔以纽约为例,探访公园、社区、道路、住宅区等市民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地方,思考新冠大流行以来,在时势的不断变化中,这座世界城市怎样运转,并在发展的难题面前通过制度创新的力量来寻求突破,在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居民之间以对话来达成协作。
特别是在纽约市政府预算局工作的一年里,亲历了以公园为主的几百个各类城市建设和运营项目的预算审批,以此为窗口,罗雨翔对城市建设的逻辑进行了探究。他的思考和经历,给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经验。
预算分析师需要很聪明
罗雨翔现任美国JLP D城市规划与地产咨询公司总监,他曾在哈佛大学取得建筑硕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区域经济发展硕士学位。本科毕业设计期间,他到各地调研,青年旅社的玩伴里有一位斯洛文尼亚经济学者,在聊天中,他建议罗雨翔去了解经济学,这会对理解城市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所帮助。
毕业后,罗雨翔加入纽约市预算局(全称“纽约市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工作,担任分析师,亲眼见证了政策和经济怎样影响一座城市的实体空间。
纽约是美国“最能花钱的城市”,市政府的预算比佛罗里达整个州都多。预算局负责审理、制定和支配政府的预算,大到制定市政项目的建设计划,小到批准政府部门购买用品,都是预算局的工作。
罗雨翔告诉第一财经,那一年他经历了很多项目,工作量相当大。但在工作之外,他也有固定的时间,可以用来研究、写作。
纽约预算局有大概400名分析师,按照政府职能部门对口的原则,划分成很多个组。比如,纽约公园局负责公共绿地和游乐设施,预算局设有“公园工作组”,专门管理公园局的预算。“交通工作组”“住宅工作组”分别对应交通局、住宅开发局的预算。

罗雨翔所在的公园工作组有6个人,管纽约所有公园的开发建设,一年的总量相当大。除了建公园外,公园的运营开销也需要预算审批,一直细化到公园公共厕所卫生纸采购项目。组长告诉他,要比伸手要钱的部门更聪明,要不断提问查明需求,分析每个新需求的内部逻辑、价格运算和政策意义。
书中提到,预算局分析师“像是侦探”,罗雨翔就是“纽约公园建设预算侦探”。纽约的公园有的属于私人组织,有的属于政府。只要是由公共财政承担运营的公园,活动运营的支出必须跟预算局打交道。范围比较大的公园、地位重要的公园,相关开支也要经预算局批准。
预算局不直接搞建设,而是从预算和政策的角度去管理对应部门的工作。“我们会看到他们想建的公园是什么样子,去决定是否批准。”罗雨翔说,“有些项目会涉及公园局、交通局、环保局的协作。交通局管道路,环保局管下水道,如果公园有些功能区正好处在马路中间的三角形地带,下面有下水道,就需要三个部门协作。预算局向这个项目批钱,由公园局来统领,负责去和另外两个部门协调。”
在预算主管面前,分析师还会转变成手中好项目的“推荐者”,代表对应的市政部门来向预算主管要钱。分析师代表的技术理性,跟主管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公共资源分配逻辑,还要再来一次较量。如果还能过关,就等着市政厅批准和公布了。
项目建设的落实和反馈由公园局按照自己的评估标准来做,并不会动态地向-预算局报告,但也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引出了书中提到的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点。罗雨翔经手过的一个公园项目的预算草案,由于选举期间的政治考量被撤回,这使他从深层次去思考纽约城市建设的经济和政治逻辑。
从预算局的角度看,预算应该做得精准,每年要花的钱,对应专业设计团队提出的时间表。但是公园这类基建项目的周期比较长,比如4年要建设一个投资100万美元的公园,每年投入25万,在政治上会显得出资太少,但100万全投在第一年则是不准确、不真实的。最终会怎么办,还取决于复杂的政治因素。
户外公共空间的深远影响
自新冠大流行发生后,纽约的城市空间有非常大的变化。以公园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就是其中的一个亮点。罗雨翔在书中用了五章的篇幅去介绍纽约的各类公园,既有高线公园这样的全球明星,也有私人公园这种私密地带。
罗雨翔提到,疫情之后,最关键的一点是纽约人意识到了户外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城市通过政策调整,促进公共空间发生变革。“开放街道”政策让人行道和步行街增加,“开放餐厅”开辟外摆位,则平衡了人们出门消费、社交的欲望和商铺的营业需求。
疫情期间,纽约人口密度高,聚集感染风险大,但又没有办法实施全域管控。政府考虑居民的出行需求和健康安全,决定多创造一些公共空间,让人不用挤在狭窄的人行道上。从最初紧急封锁300条临近公园的道路,禁止行车,专供市民室外活动,到面向社会接受申请,让民间社区组织、学校和商铺自由申报封锁所在道路,将其转为“步行街”,纽约的做法逐渐固定了下来,很多经过精心策划的活动在开放街道上举行。
罗雨翔认为:“这是公共空间、城市格局的一种深层变化,大家意识到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并且意识到不一定每条马路上都需要行车,有些路变成人行道挺好的。”他在书中提到,纽约的政策体现了保护弱势群体的进步主义价值观,穷人聚集的社区周边植被、开放空间比富人区少,“在一些公园相对较少或是人行道狭窄的高密度区域里,开放街道这种参与式的决策机制可以帮助那里的社区、店铺和居民,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资源”。

2020年4月,纽约餐饮行业就业人数比3个月前减少三分之二,行业受疫情冲击强烈,州长命令禁止餐馆在室内营业,只能做外卖,营收锐减。“国外的外卖平台没有国内这么发达,政府就允许店铺在马路边、人行道上搭个棚子,做一些‘大排档’,开设外摆区。”罗雨翔说,2020年6月提出的“开放餐厅”政策,也使城市肌理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突然纽约变得像巴黎”,“纽约以前没有户外用餐的文化,疫情之后,这成为这个城市改不掉的一个新习惯”。
书中分析称,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这两项政策,本质是关于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政策以应对疫情的姿态,创造出了新的市民权利,虽然是政府发起的新政策,但民间是参与政策落实的主体,纽约市交通局接受申请、安排抽查即可。
这些做法一方面吸引到很有创造力的人挺身而出,比如曼哈顿中国城的非营利组织“心目华埠”、布鲁克林区的公益组织“游乐场咖啡店”等,他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另一方面,也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比如开放街道和开放餐厅附近的居民可能会被噪音、气味、垃圾等影响。政府、企业和社区如何在新的政策和新的空间中相互磨合、重建信任,是这座城市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关键。
“创意的出现需要多元化的观念,一些困难的存在也会成为动力。如果太容易,那也不会很有意思。”罗雨翔说。
2023城市上市公司“密度榜”:北京冲刺500 ,上海增量第一,这省前十占三
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量前十名城市依次为:北京(475)、上海(446)、深圳(425)、杭州(228)、苏州(218)、广州(155)、南京(124)、无锡(123)、宁波(120)、成都(118)随着2023年落下大幕,地方上市公司数量的年度排名也尘埃落定。去年是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第一年,A股IPO上市竞争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锤子财富2024-01-03 18:02:470000塞航逆势开航上海: 国际航线的风向悄悄变了
2024年以来,中国的国际航线发生了不小的结构性变化。欧洲到中国的空中通道再度加密。塞尔维亚航空近日开通了贝尔格莱德直飞上海的定期航班,这与中塞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往来不断加强不无关系。锤子财富2025-02-05 01:50:550000智界S7即将开启预售 华为汽车概念股表现活跃
截至发稿,苏奥传感、凯众股份、天音控股涨停,腾龙股份、兴业科技等涨幅居前。11月7日早盘,华为汽车概念股表现活跃。截至发稿,苏奥传感、凯众股份、天音控股涨停,腾龙股份、兴业科技等涨幅居前。消息面,11月6日,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表示,华为智选车业务首款轿车智界S7即将登场,将在智能、安全、舒适、性能等各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据悉,智界S7将于11月9日开启预售。锤子财富2023-11-07 11:16:290000德国经济年末悲观情绪弥漫,2024年会好转吗?
德国的预算危机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阻碍欧洲经济。年末,悲观的经济情绪在昔日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内部弥漫。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12月商业景气指数回落,从11月的87.2点下跌至86.4点。此前,该指数连续两个月上涨。锤子财富2023-12-26 18:49:350000片仔癀,还能“涨得动”吗?
三年不涨价,一涨近三成。拥有独家大单品,片仔癀的业绩在每一次锭剂涨价后股价和业绩表现不俗。但如果没有研发的持续投入和第二曲线的增长,能否只靠独家大单品涨价来提升业绩,市场声音纷纭不一。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