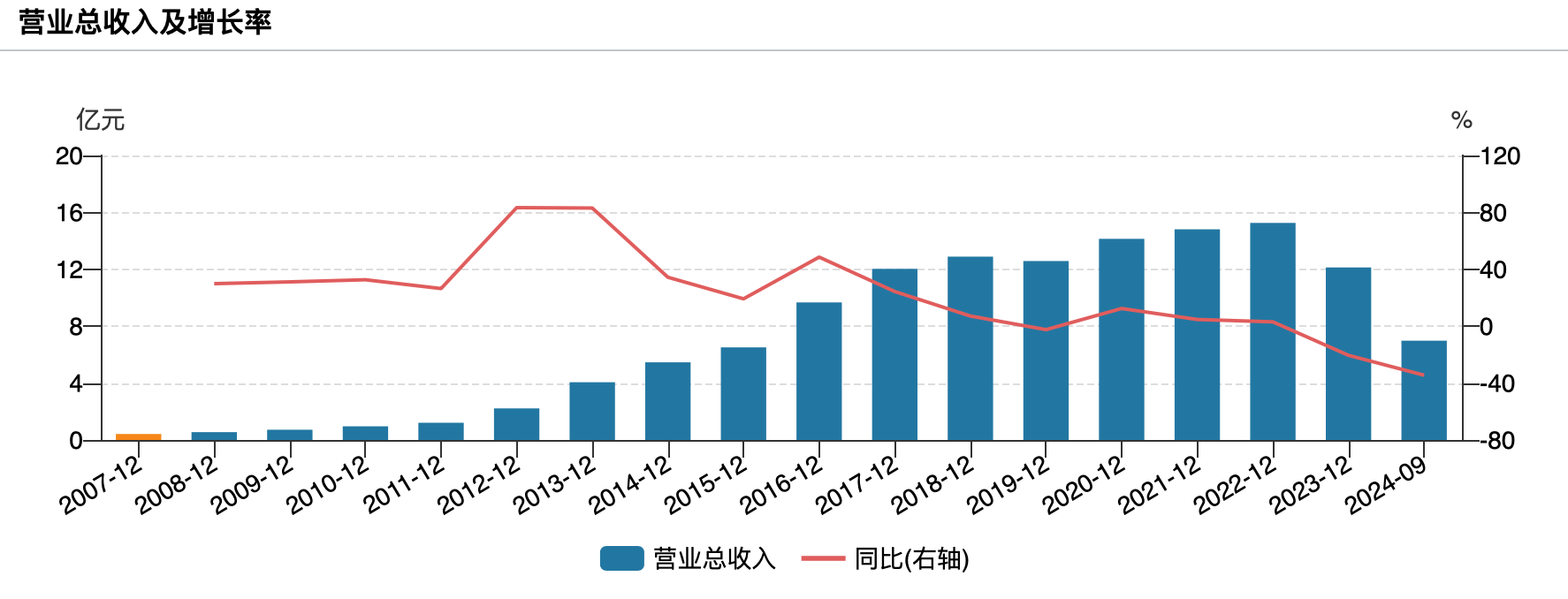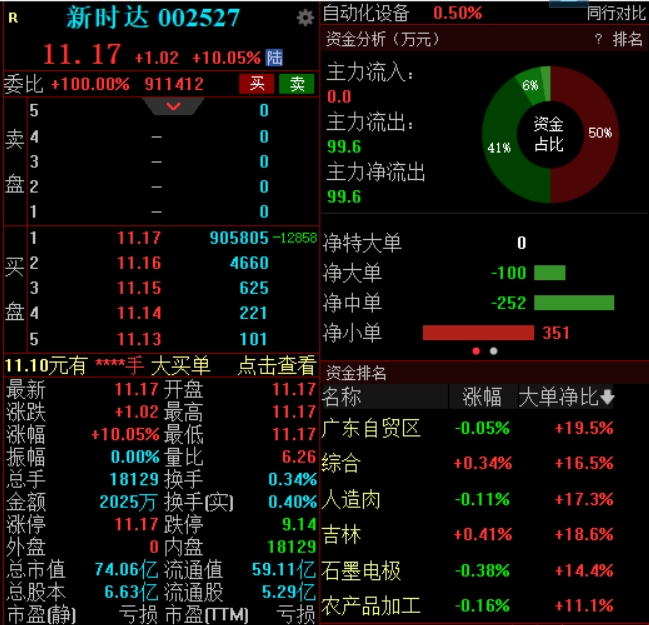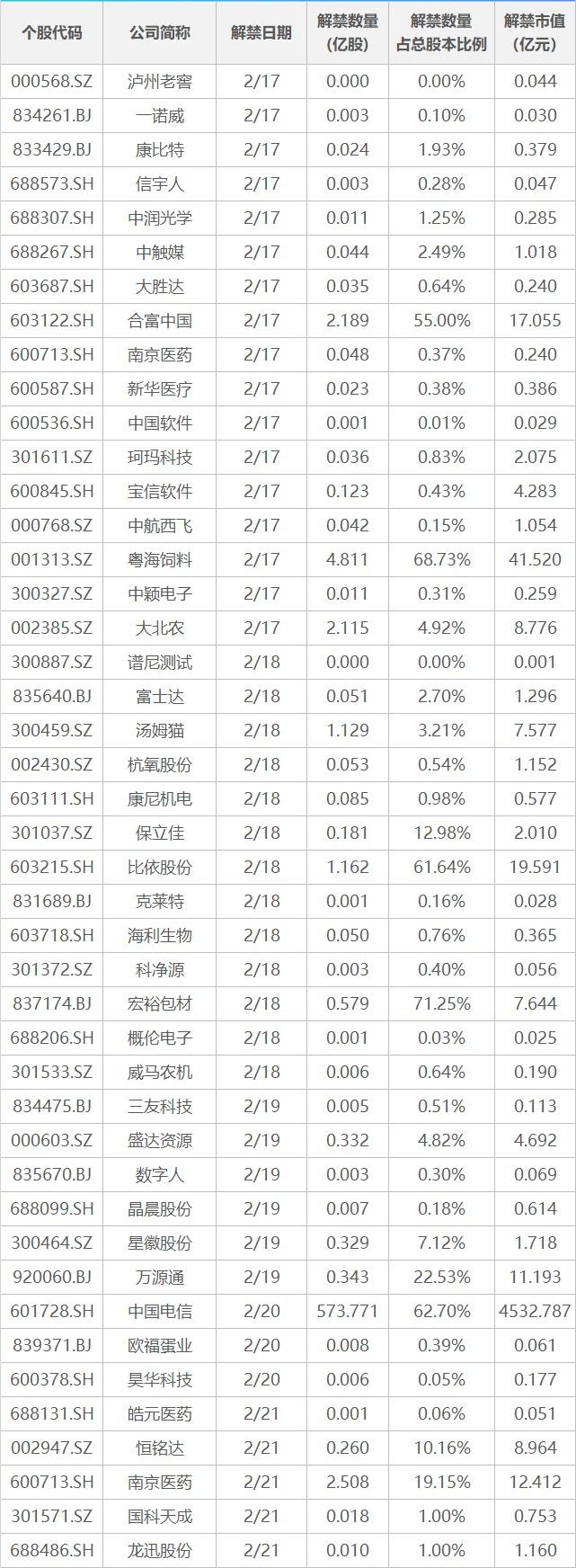100年前,一个英国作家如何书写困境中的印度之行
“我想爱上一个强壮的下层社会的年轻人,我想被他爱,甚至被他伤害。”E.M.福斯特在一则日记里写道。这位小说家最重要的作品《印度之行》,问世至今整100年,在各种上世纪伟大小说排行榜上,此书据有牢不可动的一席之地,大卫·里恩改编的同名电影也是史上经典。福斯特花了11年时间写它,完稿后一直到去世,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再无小说产出,而且,他那“爱上一个年轻人”的隐秘欲望,也在书成之后消退了。

写作困境中的“印度之行”
福斯特是英国人。1849年英国清除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完全殖民了印度全境,30年后福斯特出生。他比另一位英国作家毛姆晚生5年,都活到91岁,也都是公开的同性恋(虽然毛姆曾结婚并育有一女),不仅如此,当毛姆在20世纪初大红大紫,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作家时,福斯特也不遑多让,从1905年到1910年,他连续写成4部走红市场的小说,成为英国文坛另一知名的人物。读者们发现,自己希望有所寄放的同情心,可以稳稳地落在福斯特开辟的故事空间里;尤其是1908年问世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不仅小说本身和电影改编都十分成功,书名也早已成为大众习语的一部分。
但是,就在他的第四部小说《霍华德别业》出版不久,年方32岁的福斯特就在他的日记里吐露出沮丧。“我无能为力,”他写道,“我唯一能写和可以写的主题——男人对女人的爱,女人对男人的爱,现在令我厌倦了。”他继续写一本定名为《北极之夏》的新书,写了一半宣告放弃。他决定去旅行。
那时的毛姆早已把旅行当作家常事,在旅途中他驾轻就熟地写戏剧,同时为小说积累素材。1908年,当毛姆有4部戏剧同时在伦敦上演,他的大名出现在每一张大报的版面上时,他一面数着地中海上的希腊岛屿,一面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下成功带给他的冷峻体会(“我觉得成功对我没什么影响。我讨厌贫穷。我讨厌省吃俭用量入为出。”)的时候,福斯特还没有真正享受过一位“大英作家”在旅行方面的巨大便利。毛姆对相貌和出身都自卑,成年后拥有了一种通透的世故感,无情地蔑视被他俘获的读者和观众,相反,出身富裕的福斯特反而难以树立充足的自信,这大概足以证明上天的公平。到1912年,福斯特开始认真地筹措一次远行,他把陷入创作困境后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上面。
但选定印度作为目的地,又不只是因为想要减压。他在1906年就与印度有了缘分:他遇到一位出身高贵的印度学生穆罕默德·马苏德。虽然他的表白被对方拒绝了,但他从马苏德那里获得了一些印度的关系。带着对马苏德的单恋,福斯特从1912年10月抵达,到1913年4月才离去。半年时间里,他走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人。通过书信和日记,他把那些震撼了自己的时刻逐一写入,比如说,在西姆拉,他参与了一场“进步的”穆斯林婚礼,男人们在阳台的一端祷告,另一端摆着一大个留声机,留声机里传出无聊的英文歌——这种英国人“文明教化”的结果,固然比康拉德《黑暗之心》中描述的西方人对西非资源的暴力掠夺要温柔得多,但也足以让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觉得滑稽。在拉合尔,福斯特认识了一位戈德波尔先生,这个人领他去公共花园散步,还给他唱歌。在海德拉巴,马苏德的一位朋友大声咒骂英国人说:“不管是50年,还是500年,早晚要把你们赶出去!”
类似的情节,《印度之行》的读者日后都能在书中读到,宗主国的人带着对殖民地的想象去到那里,必然要发现现实与心想的不同,福斯特很想在这里做文章,他在1913年刚回英国就动笔了,但是,要把滚烫的一手经验转换成一篇有情节、有结构的第三人称故事(而非第一人称游记)殊非易事,再者说,他必须面对和着重处理的,还有他个人的情欲。
遮掩的情欲与矛盾的异域
D.H.劳伦斯也好,毛姆也好,这些从维多利亚时代跨入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名作家,都在情欲方面有过不失张扬的实践。劳伦斯视情欲若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认为在漫长的维多利亚世纪形成的英式风俗和秩序下,一个人只有发现并释放自己的真实欲望时,他才算得上是个人。劳伦斯对于一战期间的征募厌恶至极,军医在体检时用手摸他的下体,让他恶心到想要掀起一场暴动。而福斯特呢?他想用一只胆怯的手,去触摸一个激发了他万分柔情的男人,他相信想要真正“接触”一个人,唯有经此途径。福斯特1970年逝世,他绝对想不到,半个世纪后的人们会兴起无爱无性、宅居度日的风气,想在一张过于发达的联络之网上躲藏起来。
不过悖论在于,情欲萌发的时刻大多意味着受挫:一个人,往往是在期待落空的时候,在被拒绝的痛苦之中,对自己想追求的是什么形成了坚信。福斯特可能是在1906年被马苏德拒绝时第一次认识自己的。据《福斯特传》(2010年初版)的作者温蒂·莫法特所说,在去印度之前,他只是向一位知己弗洛伦斯·巴杰尔吐露了自己是同性恋,对性格胆怯却又执迷于情欲的福斯特来说,快感的追寻只能是鬼鬼祟祟的,然而在小说中,可以感觉到他对此情不自禁的表露。
细腻、暧昧、有象征意味的细节,遍布《印度之行》各处。影子、声音、建筑的远景、不言明的心情、深而古老的洞穴、黑暗中不知何来的暴力……福斯特用这些来营造气氛,而在情欲体验中最常见的现象——从期待和温情急变为怀疑、嫌恶,从兴奋迅速滑落到羞耻和自卑——也撑起了书中人物之间的一场场对手戏。
一个印度人和三个英国人:阿齐兹医生——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印度穆斯林及鳏夫;西里尔·菲尔丁先生——一个英国无神论者和人道主义者,有很多印度人朋友,最有福斯特本人的性格特点;另两位,一是摩尔夫人,到印度来看自己的儿子罗尼;二是年轻的阿黛拉·奎斯特,是罗尼的未婚妻。阿齐兹先后和三个英国人交好;其中,摩尔夫人初来乍到,却坚持不用偏见来看印度人,在认识了彬彬有礼的阿齐兹后,她还设法影响阿黛拉,而阿黛拉也没有偏见,除了炎热的天气令她不适,她在印度最讨厌的人是那些傲慢的英国人。
罗尼是大英殖民者官方态度的代表:“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表现得温文尔雅,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主持公道,维持秩序,印度不是一个客厅。”摩尔夫人就说他“说话像上帝”;阿黛拉也不满,考虑不愿嫁给罗尼,不想生活在他那个世界里,跟那些庸俗不堪的英国夫人混在一起。阿黛拉把印度的一切都看得神秘,想尽情地接触。跟摩尔夫人出于理性的宽容相比,阿黛拉对印度的好感,主要是出于一种浪漫化的想象和激情。
而菲尔丁,他开明、热情、从容至极,邀请阿齐兹和两位英国女士到府上一叙。阿齐兹先到,刚巧菲尔丁正在换衣服,他在门帘里面,阿齐兹看不见他,却听到了声音:我有个金领扣,不小心踩坏了。阿齐兹的反应很快,立刻说,身边正巧多余一个领扣,可以送给菲尔丁。而实际上,阿齐兹是把自己衬衫上的领扣拔下来给的菲尔丁,而这个领扣还是他妹夫送他的礼物。
阿齐兹也并非要讨好英国人,正相反,他只是出于穆斯林的热情,想交朋友而已。然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爱物,他就会对菲尔丁有所期待,当他向菲尔丁说起当时正流行的后期印象派,得到菲尔丁嫌弃的回答(“后期印象派!我真看不懂这个世界。”)时,他误解了,他以为菲尔丁的意思是:你一个印度人,有什么资格谈论后期印象派。
人跟人之间并不是只要有了相交的诚意和愿望,就能如愿以偿的。人的性格、文化习俗、语言习惯等都会影响友谊的达成。阿齐兹接着迎来了与阿黛拉的交往,在印度教信徒悠悠然的歌声中,尤其是在摩尔夫人的陪伴下,阿黛拉和阿齐兹都分外放松,很快有了信任。阿齐兹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事,讲印度历史上的莫卧儿王朝,讲芒果种植,讲他自己做过的外科手术,并说,欢迎几位都到他家去做客。仅仅是出于交朋友的激动,阿黛拉立即问起了他的住址,然后说:“太好了,我终于可以知道一个真正的印度人家里是什么样子的了。”
阿齐兹的家里很破旧,苍蝇乱飞,但这还不足以让他闻言发窘:是阿黛拉的不通世故,对客气话的照单全收,以及无意中再次强化了阿齐兹印度土著的“他者”身份,让阿齐兹措手不及。友谊真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起来的。当罗尼赶来,指着阿齐兹缺少袖扣的上衣,斥责那几位英国人跟一个衣冠不整的印度人来往时,他的无知无礼不仅使他自己丢丑,也令其他三位英国人觉得,自己和阿齐兹之间,并不能如自己所愿的那样轻松地接近。只要有殖民和被殖民这一关系存在,处在两边的人,就不可能真正自如地社交。
福斯特在另一则日记里写到过:“跨越收入、种族和阶级的障碍,获得信任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奖赏”,他笔下的菲尔丁正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一腔善意的菲尔丁,不能阻止阿齐兹产生自卑和幽怨。接下来,故事该如何发展?
电车售票员和宫廷理发师
福斯特写得非常累。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被派往埃及采访战争伤员。埃及那时也是英国殖民地,他带着已经写好的稿子,写了又改,改了又写。1917年,他在亚历山大成功地交上了一位情人,是个电车售票员,名叫穆罕默德·阿德尔。但是在日记里,福斯特写下了他切身体会到的信任之难。身体再亲密,“收入、种族和阶级的障碍”在人的心中筑起的墙垣,却是难以逾越的。福斯特记下了阿德尔的一句话,一句极为不自然的话:阿德尔说,是你的情欲使你结交了一个电车售票员。
后世的研究者总是对他这段经历特别感兴趣。2014年,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借用福斯特那本流产小说《北极之夏》的书名,以福斯特写《印度之行》为主题,创作了一部虚构作品。加尔古特认定,福斯特是在1917年遇到阿德尔时才初尝性的果实,这之后,阿德尔娶妻生子,两人虽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再要相遇就很难了,但是福斯特用阿德尔取代了马苏德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去描绘阿齐兹医生这个形象。和阿德尔一样,阿齐兹满心以为,他三生有幸地遇到了几个开明的英国人——阿黛拉、摩尔夫人和菲尔丁,他期待真正的信任和友谊,可福斯特要写出一个深刻好看的故事,就不可能让他轻易如愿。
1921年福斯特第二次去印度,这一次,他的身份是给殖民次大陆的一个小邦国德瓦斯的马哈拉贾(政治首脑,也称“大君”)担任秘书,在此期间,他在大君的默许之下,搭上了一名宫廷理发师。福斯特写下了自己微妙的心理变化:
“第三次见面时,卡纳亚(理发师的名字)很准时……我立刻对他产生了兴趣和柔情,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我无法从卡纳亚那里得到埃及人(指阿德尔)那样的情感反应,因为他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奴隶……我现在在与他的关系中掺杂了一种欲望,想要对他施加痛苦……我从未和其他人有过这种欲望,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我并不是想惩罚他……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奴隶,而我是一个没有人可以追究的暴君。”
这就是亲密关系的真相:只要有一方不够投入,另一方的爱恋瞬间就会变成莫大的羞耻,因为他觉得自己交出了最软弱的一面,却遭到了辜负。这里面必然少不了误解,毕竟一方不可能控制另一方对他的感受,如果无法给出对方所期待的“反应”,他也无从辩白。
福斯特之后的确对理发师“施加痛苦”了——在大君的鼓励下,他打了卡纳亚,只不过起因是卡纳亚对外吹嘘他和一个英国明星作家的关系,想要提高自己在宫廷里的地位。大君告诉福斯特,对待这种下等人,暴力是唯一的交流方式。于是,一心渴求“接触”的福斯特穿上了英国人的制服,拿起了皮鞭。
这些都是福斯特自己记下来的事情。温蒂·莫法特的传记,在写到这里时为他开脱说,这场暴力成了他反思权力、反思种族主义和帝国行为的契机,福斯特一时间把卡纳亚想象为没有情感的下等人,但他为此深深负疚。也许这样的理解是对的。不过更重要的是,从结情埃及的电车售票员,到鞭打印度的宫廷理发师,这些经历对福斯特最终写成《印度之行》的高潮桥段——马拉巴尔洞穴事件,构成了决定性的影响。
作为隐喻的马拉巴尔洞穴
福斯特曾说:昌德拉波尔的马拉巴尔洞穴“代表着一个可以集中注意力的地方”。这组迷宫般复杂的洞窟,在他的笔下,蕴藏了深不可测的神秘智慧;从洞穴中回来的游客“不能确定他的体验是有趣的还是沉闷的,或者干脆就没有任何体验”。他发现,很难讨论这些洞穴,也很难在脑海中把它们区分开来……洞是存在的,但洞也是空无,洞穴作为“景点”的响亮名声并不取决于人类的言语,无人讲得出它的好处。
在《印度之行》里,为了化解阿黛拉对他家产生好奇而引起的尴尬,阿齐兹提议一行人去游玩马拉巴尔洞穴。阿黛拉深受吸引,菲尔丁和摩尔夫人也都欣然愿往。阿齐兹花了一大笔钱来筹备所有人的出行,可是菲尔丁没有赶上火车,然后,在靠近山洞的时候,阿齐兹安排两位女士骑一头大象前去山洞,这个安排也引发了误解,两位女士觉得自己被阿齐兹当成了一般庸俗的白人游客。不愉快的感受在积累。到了洞穴里,摩尔夫人被一种回声击中——它的“嘭”音单调而毫无特色,却使摩尔夫人的基督教信仰在此动摇了:她顿悟道,爱,无论是发生在神圣庄严的教堂婚礼上,还是发生在最原始的山洞里,在这一记回声面前,好像没有任何区别。洞窟里的回声是原始的,先于一切而存在,当然也先于人创造和信仰的神。
她退了出来。而阿黛拉还想接着逛,于是阿齐兹带着她,跟着一名向导进去。他们一边说着话,一边各想着心事。到了洞里,二人无意间走散了。接下去就是一阵响动,是惊吓,是奔逃,是呼救。阿齐兹先是发现了阿黛拉摔坏的望远镜,然后看到她被一辆车接到山脚。他们再次相聚时,警察也赶到了,告诉阿齐兹:阿黛拉已经控告了他,说他在山洞里对她非礼。
几个人的命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接下来的庭审也写得非凡,阿黛拉在庭审中再次被印度人的鼓声所感染,她再度眩晕,放弃了控告,而且透过福斯特精妙的文笔,读者似能觉察到,阿黛拉对阿齐兹别有一番心情。阿齐兹是否真的袭击了她,不仅法庭判定不了,她自己都不清楚,也许袭击出自她的想象,也许她是因为爱上了阿齐兹却无法说出,也无法付诸行动,而产生了被阿齐兹施暴的幻想。真相是不可知的,他们两个的“接触”,被置于一段黑暗的洞穴通道里,而隐喻性极强的“通道”,正是《印度之行》(PassagetoIndia)书名里的关键词。
各种可能性都被这个通道所涵盖,福斯特似乎想说,唯有在充满了“嘭”声的绝对黑暗之中,才可以抵达印度,这个印度,对英国人而言,不只是一块可以猎奇享乐的殖民地,更是一个让他们得以面对自身、审视自身的异域,一如书中的摩尔夫人那样;而对福斯特本人而言,印度是他的情欲所施向的目标,而自信与自卑、柔情和羞耻,在黑暗中会发生难以预期的转化。
1925年1月初,出版不久的《印度之行》已获得一片赞誉,福斯特却在日记里用朦胧的词语缅怀他1921~1922年间的第二次印度之旅,那是他情欲释放最为狂乱的时刻,但阿德尔也在那期间因肺结核去世。永失所爱的福斯特预感到,他在情欲这方面已过了巅峰而见衰,由此导致的空虚和抑郁,仅能指望名声和财富来抚慰了。这不仅是福斯特,也是世上每个凡人的命运。

《印度之旅》(插图珍藏版)
[英]E.M.福斯特 著,[日]吉田博 绘
九州出版社·后浪 2023年12月版
商务部答一财:希望G7将不寻求对华脱钩的表态落到实处
束珏婷称,不能一边说不寻求脱钩,一边滥用贸易投资限制措施,打压遏制中国发展。在七国集团(G7)峰会上,G7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其并没有寻求与中国“脱钩”,而是在寻求“降低风险”。对此,商务部发言人束珏婷在25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希望七国集团成员将不寻求对华脱钩的表态落到实处,不能一边说不寻求脱钩,一边滥用贸易投资限制措施,打压遏制中国发展。”锤子财富2023-05-25 17:10:510000欧晶科技再融资6.2亿元,一季度净利“狂揽”超去年整年的七成
从今年一季度的成绩单来看,欧晶科技一季度的营收接近去年营收的一半(44.35%),一季度揽收的净利润超过去年净利润的七成(72.27%)。4月21日,欧晶科技(001269.SZ)公告称,拟发行可转债募资不超过6.2亿元。欧晶科技方面表示,本次募资的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投资于宁夏石英坩埚一期项目、宁夏石英坩埚二期项目、宁夏切削液在线处理项目和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营运资金。锤子财富2023-04-21 15:47:270000北交所转板新规落地,补充完善转板事前审核程序
北交所《转板指引》发布后,有转板意愿的上市公司可依规开展选聘保荐机构等转板相关工作。北交所改革举措再迎新进展,备受市场期待的转板新规正式落地。10月8日,北京证券交易所(下称“北交所”)发布了修订后的《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7号—转板》(下称《转板指引》)。《转板指引》发布后,有转板意愿的上市公司可依规开展选聘保荐机构等转板相关工作。0000上海市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还研究了这些重要事项
会议听取和审议2025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立项工作情况并指出,要聚焦暖民心、解民忧,努力把民生实事办得更好。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16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在市委领导下,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上海落地见效;部署做好2025年为民办实事工作,推动东方枢纽及周边地区规划建设。0000通富微电获主力加仓超16亿元,三机构净买入3.59亿元
从主力资金流向来看,通富微电今日获主力资金加仓超16亿元,净流入额居两市个股之首。5月29日,截至收盘,通富微电涨停,报24.21元,成交额46.11亿元。该股股价月内持续反弹,累计涨超35%。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深股通买入通富微电3.57亿元并卖出1.21亿元,3家机构净买入3.59亿元,1家机构净卖出2947.27万元。锤子财富2023-05-29 17:39:2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