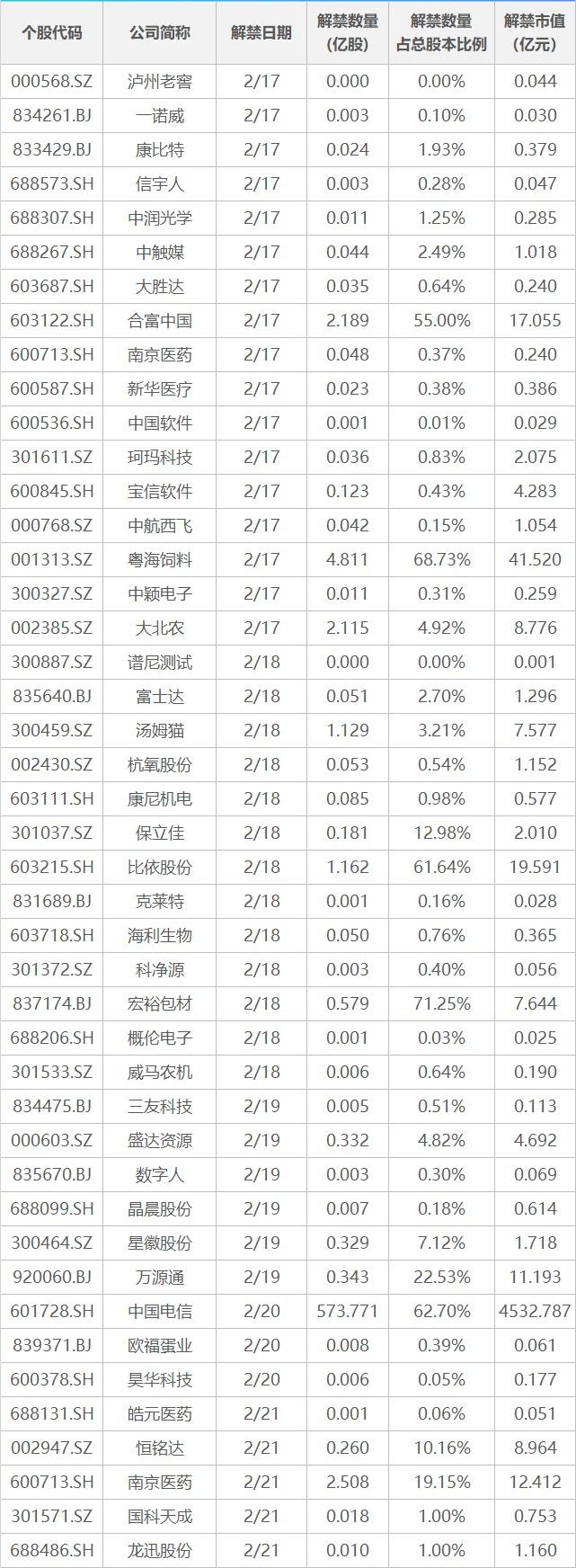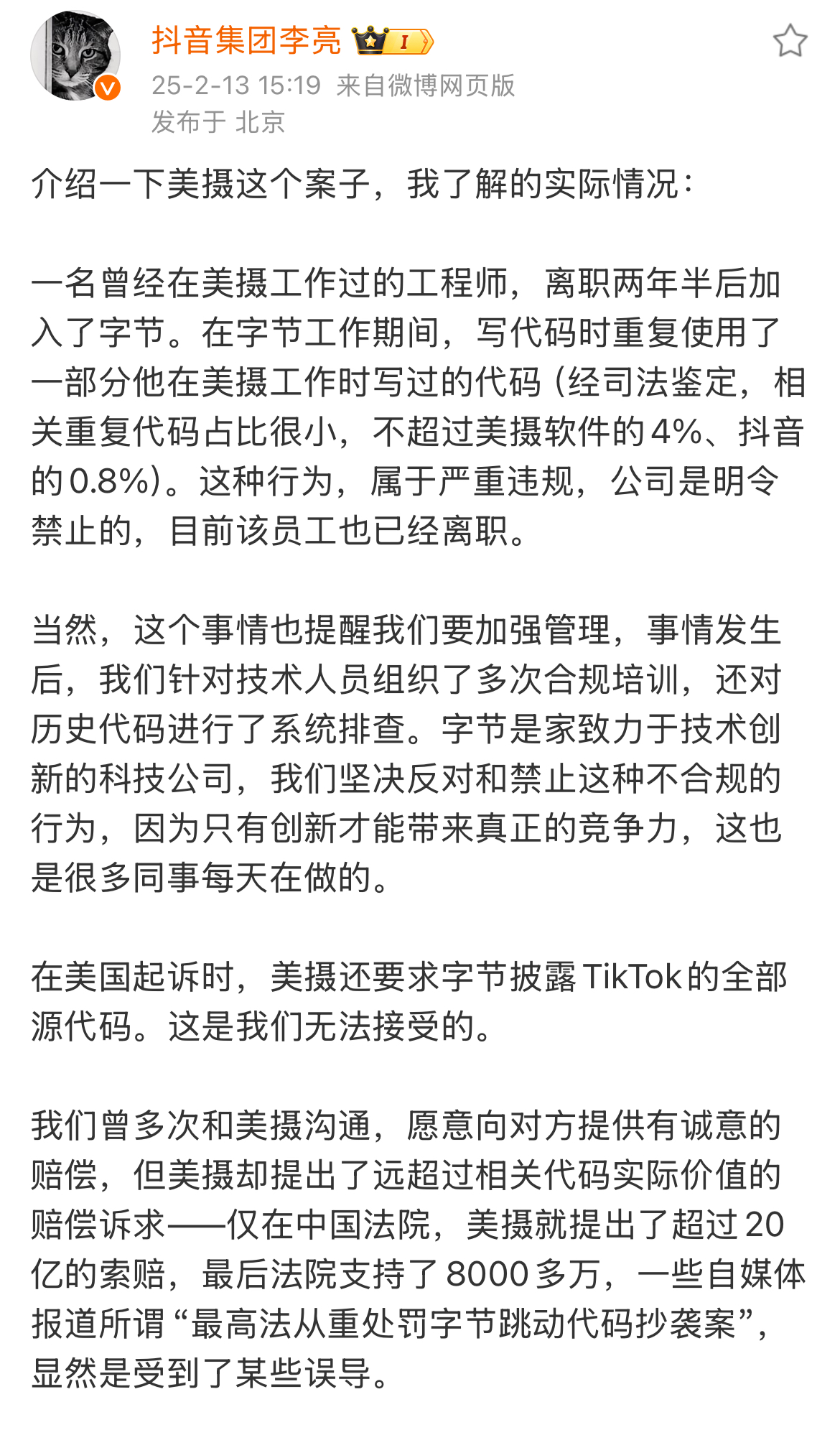民谣诗人张玮玮,在音乐中与中年危机和解
新专辑《沙木黎》上线前一天,张玮玮像往常一样去了工作室,内心却涌动着焦虑。他不知道,这张耗费三年时间做出来的电子民谣,会收到什么反馈。
如今,三个月过去,他的心态已经完全松弛,落了地。新专辑巡演走过上海、广州等六座城市之后,12月25日是北京站。他将在一场静谧如梦境的舞台上,回望1997年初到北京闯荡音乐梦的自己。

过去三年,张玮玮从社交圈消失了。那张带给他诸多关注度、被誉为中国民谣圈近十年最好作品之一的《米店》,给他带来“民谣诗人”的赞誉,又被他全然抛在身后。
他放下木吉他和手风琴,扎进电子音乐制作人严俊的工作室,从头开始学起,把复杂的合成器融入民谣音乐的叙事中。
《沙木黎》是一张既不民谣也不电子的专辑,仅属于张玮玮。它广袤而浩瀚,温暖且神秘。每一首歌词,都是精炼隐晦的现代诗,蕴含多重虚幻的、遥不可及的深意。作家韩松落将专辑听了上百遍,觉得这是一张玮玮个人的佛音,每首歌都寄寓了心灵,如同房屋寄寓了人的身体。
在《沙木黎》里,张玮玮把横亘在民谣和电子乐之间的那道墙推倒。他要让听电子的人听到民谣,让听民谣的人听到电子。
打破、推倒、重建,再打破,再重建,是张玮玮音乐生涯的常态。
21岁,他从家乡白银买了火车票,一路北上“搞音乐”。在传奇的河酒吧,他与中国民谣最初的一帮音乐人小索、小河、万晓利一起,在民谣乌托邦的年代,喧嚣着彼此的青春。那些年,他为野孩子、美好药店与IZ乐队担任乐手,又与导演孟京辉合作戏剧。
30岁,随着民谣乐队纷纷解散,张玮玮面临危机。他意识到,音乐的梦是属于歌手的,“做乐手只是在别人的梦里,当别人梦醒,你就没地方飞了。”为了延长自己飞翔的长度,他几乎是被迫开始写歌。被无数文艺青年传唱的那首《米店》,就创作于“从乐手转型歌手”的低谷期,他说当时的自己,“没名没利,心里很干净,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感里写歌。”
35岁,他离开待了14年的北京,搬到大理定居。随着《米店》的火热,演出邀约突然增多,他开始奔忙在无数个音乐节之间。每次演出结束,辗转回到大理,就是疲惫、倦怠和虚无。
他选择退出乐队,在两年里销声匿迹。大理新家的房子耗费三年总算装好,张玮玮只住了半年,就再次逃离,只身去往上海,开始新的重建。
上海三年,张玮玮回避了大部分社交,把时间耗在工作室,每天写歌编曲,学习合成器。他觉得,自己就像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徘徊寻觅,找到了这张专辑。”
沙木黎是一个虚构人物,张玮玮不愿过多解释这个名字的含义,而是让它处于虚幻、宽广的时间与空间中,就像整张专辑的电子乐带来的浩瀚感一样,听上去是迷雾重重的多维梦境,却能在某一刻被突然击中。

《沙木黎》的歌词,每一首都像寓言。那是张玮玮从2019年起陆陆续续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的文字,上万字的积累,都是真实记忆。他把文字抽取出来,一点点打磨、凝练,成为抽象的、诗一般的句子。
“雨水惊醒了,山里的野蘑菇/它的生长,自由而美丽。”那是大理。
“睁开第三只眼睛/望着不同的方向/大马士革倒挂在空中/所有的故事,落下来。”那是天马行空的记忆碎片。
在他想象力奔涌的文本中,能看到他最喜欢的《哈扎尔辞典》式的魔幻拼贴与复杂意象,也能看到波兰科幻小说家史坦尼斯劳·莱姆、俄国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对他文学功底的影响。
40岁那年,张玮玮经历亲人去世,一度深陷中年危机。
“生命在流失,人总是会患得患失。好在有音乐的世界,在里面呆着,就像一个庇护所,可以化解很多东西。很多现实中不好表达的,说出来没人听的时候,变成好听的歌词,好看的歌词,自己就化解了。” 张玮玮说,《沙木黎》呈现的是人到中年的质感,“有用久了产生的色泽,也有时间留下的划痕。”
在生命的起伏曲线里,他再一次用音乐安慰自己,“留下这50分钟的声音,我很幸福。”
他感激自己能有能力从事音乐,将音乐当作慰藉和解法,直面那些困顿、迷茫的时刻。音乐在慰藉他的同时,也从他这里传递出去,慰藉到更多的人,这恰是音乐人的意义。
“我把这些年难过的事情,都放在音乐里。这些事情就过了,翻篇。”张玮玮说,待新专辑巡演结束,他将筹备第三张专辑的创作。
对话张玮玮:我的宿命,一直要在起伏里面待着
第一财经:你似乎从不愿在某一个状态里面禁锢自己。从担任不同乐队的乐手,到与郭龙组乐队合作《白银饭店》,十年后,回到一个人的《沙木黎》。这种不断打破和蜕变,是怎样的过程?
张玮玮:《白银饭店》出来后的这十年,时间过得特别快。回看自己,很多年是在蹉跎浪费。
那时候赶上音乐行业上升,演出多,特别忙,进入职业化的工作状态。参加一个音乐节,从出发到回来,前后一周,上台也就40分钟。一周接着一周,慢慢变成一种滚动,人在里面就虚了。
有些人不太会复盘,过去就过去了,那是幸福的。焦虑的人总要复盘,每次一复盘,就焦虑。站在台上没信心,演奏乐器也打动不了自己,弹着琴会走神。
做一件事好不好,要看是不是让你感受到澎湃和美好,那种力度会让人陷得特别深,哪怕是痛苦的、费劲的,也会让时间变得有深度。我改变不了生命的长度,但能改变时间的宽度,让时间更有分量。有质感的时间,是能带来结果的。
我总是折腾,去重新寻找,就是基于我必须找到能说服自己的东西,在手上拿着,让自己有信心。我得不停地拆了重建,重建了再拆,用比较刺激的办法。
只要你努力去找,一定能找到(结果)。就像淘金的人,在河边的泥沙里一点点筛,一定能筛出金子。原地待着,肯定找不到。只有走得特别远,特别累的时候,一转弯,见到风景,那是一种开阔的快乐。
第一财经:你常常对自己做音乐这件事产生怀疑?
张玮玮:自我怀疑是一直存在的,也是所有创作者都在面对的。
我是个理性的人,性格不太适合做音乐。我没法在某一个时刻说绽放就绽放。我是摩羯座,对秩序有很深的执念。工作室里,合成器的上百根线都弄得很整齐,桌面上不能有指纹,杯垫必须放在同一个位置。但音乐这个职业又是反流程、反秩序的。
自我怀疑也是神圣的一部分,怀疑了才会想,迷茫了才会找出路。我的职业宿命可能就是,一直要在起伏里面待着。
第一财经:你离开北京,搬到大理,跟野孩子乐队每天排练、演出,其实像是音乐乌托邦的生活。但你最终还是离开了大理,为什么在大理会有那么多的危机与变化?
张玮玮:大理很舒服,一年四季的气温都稳定,天气又好,让你一直待在舒适度里。在那儿生活的人,都在说生活表面的事儿,很平和、平淡。当初我也是冲着这个去的,但每个人的需求,不一定跟大理真的吻合上。
我在舒适和安全里,精神就会没劲儿。有一两年,我特别颓,总感觉困,刚睡醒就困,以为生什么病了,整天都是软软的,弹琴也弹不进去,生命力变得特别弱。
我需要谈论激情澎湃的事情,需要专注和研究一件事,需要生命的张力。恰好那时候40岁,跟中年危机撞到了一起。有时候演出完,回到家,躺两三天都不出门,很颓丧。
有个朋友来大理看我,说到我的状态,他说,“你就是太闲了。”我反驳,我们演出很多,很忙。话一说出口,自己都觉得虚。
他说的闲,是不突破自己,是原地赋闲。这句话特别狠,你流再多汗,那也是赋闲。这跟环境、跟别人都无关,自己画地为牢,不能怨环境。
我从18岁开始做音乐,那么热爱,把音乐当作信仰一样。结果我变成在台上走神的人,我就不配站在那儿。怎么做一个合格的音乐人,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能自洽的,就都是合格的。就怕你不自洽,含糊,台下的观众都能看得出。
第一财经:从2020年筹备,到《沙木黎》面世,你用“徘徊寻觅”来形容自己的状态,去了“很远的地方”。这像是一场独自一人的旅程吗?
张玮玮:我对《白银饭店》有不满,花了60%的时间去录乐器,人声就录了一周,完全搞反了。我的遗憾,只有好好再做一张专辑,才能被治愈。
2020年秋天,我决定搬到上海,除了乐器和随身的东西,什么都不拿,从头开始。
2021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严俊工作室,他是中国顶尖的电子音乐制作人,我听了一下午合成器,买了台琴回去玩,三天就明白了,这是我要找的路。
这几年,我每天都是很固定的时间创作,每首歌都写好多遍,很折磨人。对电子乐,我是初学者,不是特别能理解和消化。
我喜欢电子乐的魔力,它太宽阔了,音乐就能把空气给撑开。电子乐其实是物理加数学,一个人就是一个交响乐团,要有宏观的角度,也要有细节。做电子乐很像建筑师,需要立体思维,一个人完成旋律、演奏、录音、混音。我接下去要好好学电子乐,如果想把所有的东西掌握,需要一辈子。

第一财经:沙木黎像一个虚构的人,整张专辑里,你用现代诗的方式,在梦境里向沙木黎述说,有怀念,有歉意。这张专辑对你而言是什么?
张玮玮:《沙木黎》挖进我内心很多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告别仪式,我不再留恋和愧疚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学电子乐两年交出来的答卷。
这张专辑有多少人会听,我不太在意。就像《黑石》里的歌词写的,“有的升上天空,有的沉到海底。”它是一张纯个人的专辑,承载的都是个人化的记忆。
第一财经:谈谈你的父亲,父亲对你有什么影响?包括那些显见的(让你学音乐),和这些年慢慢显现的影响是什么?
张玮玮:我父亲是老一代文艺青年,野路子再加上经过音乐学院的训练,后来做了音乐老师。小时候,常看他一人待在房间里,关了灯,坐在黑暗里抽烟,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小时候我经常干坏事,突然有人喊,“你爸来了”,我叫大家别动。就见我爸从我们面前径直走过去,但看不见我们。他走路常常都看不见周围。
他总是抄谱子,也不看电视。在工资只有两百多的年代,他花了3000多块钱从广州买回来一台钢琴。小时候,我特烦这些,但现在,看看我在干什么,就已经说明他的影响了。
生命是一体的。他在他那个时代起了个头,我在这个时代接着做这件事,因为一个人的一辈子不够长。我就是延续他的那个人,我们一起在完成音乐。
国家网信办就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运营者在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按照《网络安全事件分级指南》,属于较大、重大或特别重大网络安全事件的,应当于1小时内进行报告。0000投入50亿美元研发“星舰”首飞爆炸 马斯克为登陆火星不计成本试错
“星舰”的研发代价是高昂的。马斯克此前估计,开发“星舰”耗资约50亿美元,并且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是来自公司内部。当地时间4月20日,马斯克的SpaceX公司尝试首次发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新型超重型火箭“星舰”(Starship),不过这次无人试飞在几分钟后因飞船在空中爆炸而告终。锤子财富2023-04-21 07:41:040000金鹿公务一季度包机创历史新高,公务机包机市场为何火了
往年的3月份,公务机运行的活跃度通常会迎来一个短暂的回调,但今年则一反常态。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优化,旅游和差旅的需求集中释放不仅带动了民航票价的提升,还把公务航空的包机市场带火了。海航航空旗下的金鹿公务董事长吴重阳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今年第一季度,公司的包机业务成交额超过1.2亿元,同比去年增长160%,执飞公务机包机航班近500班,创历史新高。锤子财富2023-04-21 15:47:2800002023年新出生人口数出炉,母婴、奶粉行业松了口气
新出生人口下降速度减慢,奶粉市场萎缩程度也会进一步放缓。今日(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的新出生人口数为902万,也让奶粉和母婴行业从业者松了一口气。在业内看来,这一数字较上年同期的下降速度在减慢,奶粉市场萎缩程度也会进一步放缓。新生人口数字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母婴市场,比如在奶粉消费中,1、2段奶粉和3段奶粉(12月以上)各占一半,人口变化对奶粉市场的影响会持续2~3年。锤子财富2024-01-17 15:27:300000台风“卡努”逼近我国东部沿海 将现持续风雨
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已进入我国东海,受“卡努”及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和海域将有持续风雨天气。今明天(8月3日至4日),东北强降雨仍将持续,黑龙江、吉林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已进入我国东海,受“卡努”及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和海域将有持续风雨天气。东北强降雨持续局地伴有强对流云南广西降水频繁锤子财富2023-08-03 08:51:3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