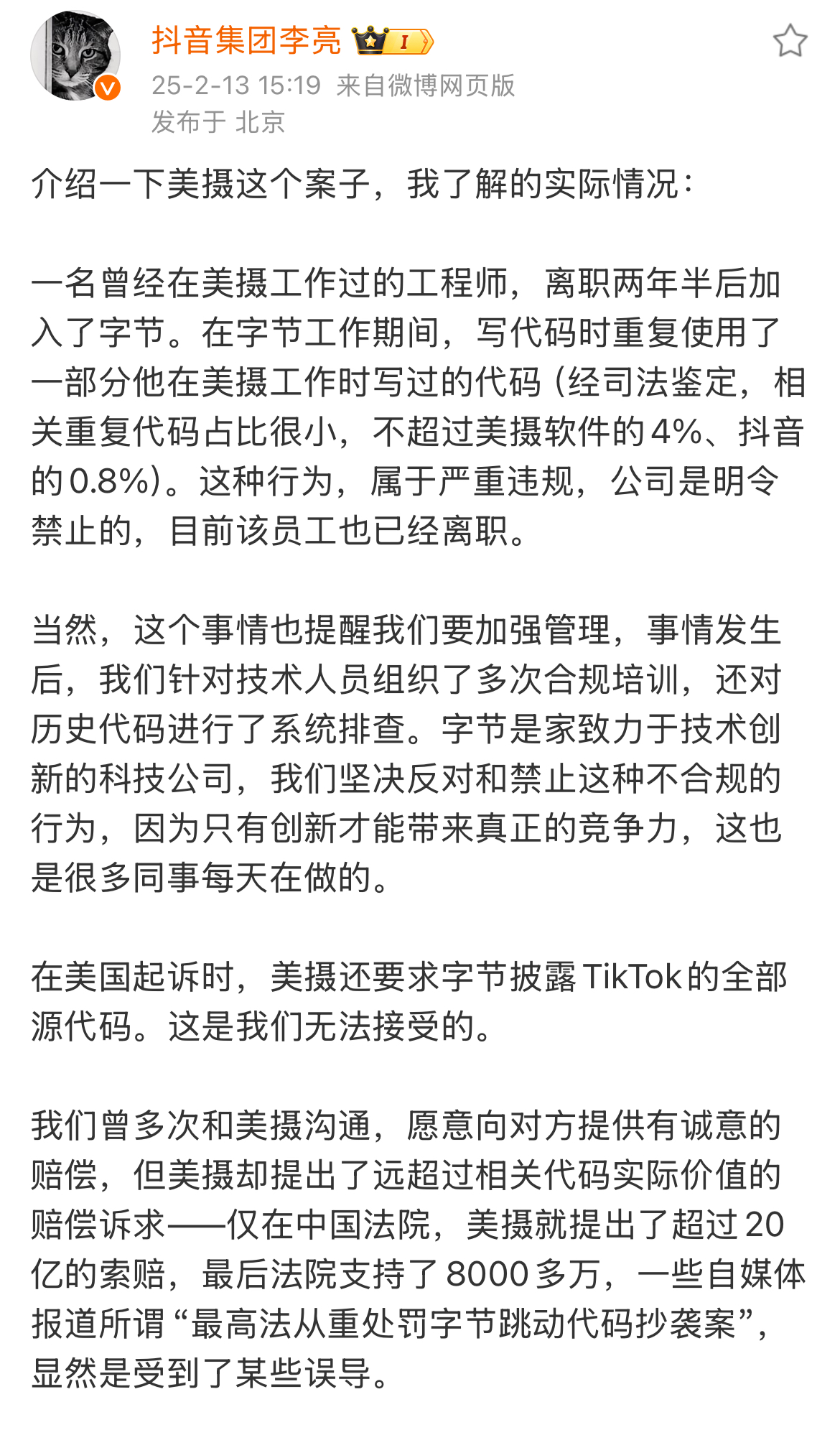中国是一个海洋观念薄弱的民族吗?
明年就是甲午战争130周年了,到时候想必网上会很热闹。甲午可能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一块永久的心病,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一遍又一遍地看了那部《甲午风云》,每次看完后心头都堵得慌,并且每一次都没来由地假设,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那样,后来的历史会怎么样。这当然是小男孩的游戏。
回到题目上来,我读过很多纪念或研究甲午的文章,发现有一个共性,就是把甲午之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传统上海洋观念的薄弱,甚至认为根本原因就在此。这让我想起某部曾经轰动一时的政论片,其中心观点之一,就是要用海洋文明、蓝色文明,取代黄土文明。黄土文明被标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它的内涵被界定为封闭、守旧、落后的农业文明;与之相反,蓝色海洋则是欧美开放的商业文明的符号。这里面有多少简单化、抽象化,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截然两分的对比只适合做口号,完全不适合用来真正地总结历史经验。

远古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心态封闭的内陆民族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虚构的。中国有那么长的海岸线,它根本不是一个纯内陆国家,怎么可能产生完全的内陆民族特性?中国本身的地域差异如此之大,你可以说西北地区比较内陆化(但依然通过青金石之路、丝绸之路等与中亚、西亚和南亚有着数千年的密切往来),可是广阔的沿海地区从来、一万年以来,就是具有非常鲜明的海洋特性的。
日本的考古专家很早就指出,日本远古的绳纹文化(距今1.3万年~2500年),很多出土器物类型特征,与浙江沿海的河姆渡文化非常相似,保守地说,它们之间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和流通,而这是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事情。更为激进的观点,在1.3万年前的绳纹时代陶器和1.4万年前中国江南如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出土陶器之间,找到了很多相似点,据认为是从江南传播到日本的。考古还在台湾、香港、澳门都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而它们的器物特征与中国内地南方,包括两广和福建的新石器时代诸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说明至少一万年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居民就频繁向海外拓殖,与海外交流。《山海经》中大量的海外描述就是一个积淀的结果。这一完全符合人类拓展本性的行动,无论是与希腊、西班牙还是后来的日不落帝国相比,都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区别在另外的方面,这需要另文论述),而且在此后数千年间,即便是受到朝廷高压限制的时代,也从未能够禁绝,这后面还要讲到。
产生这样的错误观念,即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内陆农业文明的根本原因,与另一个长期以来的错误观念有关,即简单地将华夏文明等同于黄河文明。实际上考古学界早已有共识,远古中国的文明,黄河虽然非常重要,但绝不是唯一的,甚至不见得一直是最重要的。在中国广阔的地域上,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遍布了各种高度发展而且交往频繁的文化类型。长江、珠江、黑龙江,等等,诸大河流域都有绝不逊色于黄河流域的文化类型。因此从源头上,黄河文明就不能涵盖中国传统文化。
只是因为夏商周建立了位于黄河流域的“帝国”,其中央观念和传统遂被视为正统,并且依赖中央对传媒的掌控(史官、祭器、甲骨等)得以流传后世(这种传媒的力量甚至一直作用于今天,因为我们对三代的了解和理解,多半出自官修史书、青铜铭文和甲骨文)。可是没有资格得到记载的其他观念、其他传统,可能是影响力非常强大的,因为以当时的物质条件,中央政府凭其强力,肯定只能控制相当有限的范围,范围之外,比如东部和南部沿海,最多只能以怀柔之策,让其多少听点号令,至于当地流传千年的民俗和实际生活状态,则是完全管不到的。
因此即使你从古书里翻出诸子说过什么重农轻商、重土地轻海洋的话,也丝毫不代表真正的中国传统精神是排斥海洋的。相反,如果某某子一再强调重本轻末重农轻商,很可能恰恰说明当时中国商业很发达很活跃,其中也一定包括沿海地区几乎出自本能的大量海外贸易。如果我们将《山海经》之类民间典籍提升到与诸子相当的高度,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传统中,其实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外向、探求、拓殖的潮流,它的力量至少不低于见诸“主流”的意识形态。
郑和
在王赓武先生关于东南亚和南亚经贸史以及华侨史的大量论著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数千年里中国南部沿海居民规模浩大的海外探险、贸易和拓殖。同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名的《白银资本》也以大量史料和数据表明,直到清代,甚至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依然是东南亚和南亚海上贸易的真正霸主,其霸主地位的扩张,甚至威胁到了印度洋上当然的贸易主宰——印度。南中国海贸易圈(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比那条著名的沙漠丝绸之路只会更重要,总体贸易量更大(因为水路运输通常要比陆路运输更便捷,载货量也大得多)。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欧洲通过东南亚进入中国,或者以印度为中转站进入中国。至少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因为贵族对中国奢侈品贪得无厌的追求,而造成大量“国资外流”,结果长期“积弱”,竟达千年之久。如果不是发现了新大陆,得到大量廉价的美洲白银作为与中国贸易的筹码,他们还将继续积弱下去,为后来的工业革命进行最初的原始积累根本无从谈起。我们可以对弗兰克大胆的观点详加讨论,但是无论弗兰克的结论是否有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数千年中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个民族,怎么能说它传统上海洋观念薄弱呢?
1405~1433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是人们一直在探讨的热点话题,明年又逢其690周年(和甲午130周年放在一起,真是发人深省)。但是传统观点一直认为,郑和只是带着大船和金银财宝去转一圈,炫耀炫耀武力,宣扬宣扬皇恩,安抚安抚蛮夷。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整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以中国为贸易中心的所谓“朝贡贸易体系”,事实上,这恰恰是一个完全“中国特色”的海上贸易体系,只是它的很大一部分“贸易”不是完全以商业交换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朝贡和赏赐的方式实现(详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等著作)。但尽管如此,官方和民间的纯商业贸易还是最为重要的贸易途径。前面已经强调过,最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中国南部沿海的长途海上贸易就很活跃,经过汉、唐、宋、元,到明代,整个贸易体系已经非常成熟。郑和下西洋,是水到渠成的行为。
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还在三佛齐杀害明朝使臣,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换句话说,随着爪哇、暹罗实力渐渐增强,原有的贸易体系出现动荡,开始对中国和印度的“世界贸易中心”地位造成威胁(参见《白银资本》对这一时期东南亚海上贸易状况的论述,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对此也有涉及)。郑和的使命之一,就是理顺这个风波初起的体系,安抚崛起的地区强国,重申“和平共处互惠互利”原则,当然,采取的形式是富有当时朝贡贸易体系特色的皇帝封赏和武力陈列相结合。
顺便说一下,李约瑟曾评价以郑和船队为代表的明代中国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拥有这么强大海军的,怎么可能是传统上海洋观念薄弱的民族呢?
倭寇
同样是明代,另一个与海洋密切相关的事件是倭寇。但是如果深入历史去挖掘真相,那么倭寇之灾,就远远不是“戚继光抗倭”这样简单的是非分明的事件。事实上,倭寇在明太祖称帝以前就已存在,当时被朱元璋战败的张国珍、张士诚余党,曾带领日本人骚扰东南沿海,也就是说,倭寇的老祖宗,实际是中国人自己。洪武二年、三年(1369、1370年)太祖派使臣前往日本,质问日本权臣足利良怀。足利良怀称臣纳贡,并送还明州、台州二地七十余名被掳男女。洪武年间前来袭扰的,通常只有小股倭寇,并未成为大患,尤其洪武二十年(1387年),太祖命周德兴、汤和在福建兴建防倭城,布置六七万士兵后,倭寇更是大为减少。但是嘉靖初年,明朝突然实施海禁,恰恰是这一政策,后来使倭寇酿成大患。

嘉靖海禁的具体原因,实际上也是因为和日本在进行朝贡贸易的时候发生争端,这史书记载颇详,不表。关键是随意定一个海禁的政策容易,真正要禁绝海上贸易却是完全不可能。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指出,到明代,日本(因为其为中古世界上最大的产银国之一)已经成为除欧洲以外中国最重要的白银输入国。明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繁荣的经贸活动需要大量白银来维系,而中日贸易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急需的白银资本。虽然海禁使得中日民间贸易成为非法,朝贡贸易也中断达17年之久,但蓬勃发展的国内经济对白银的需求却不是海禁所能压制的。这样,沿海地区的非法贸易,也就是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日趋活跃。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即使中央政府历来重农轻商重土地轻海洋,也完全不能抑制实际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对海洋贸易的渴望,只不过能够改变一些形式,掩自己的耳目罢了。
因不满政府的海禁政策,部分中国民众与日本人勾结,占据沿海某些岛屿,或是私下到中国沿海交易,或是采用不法手段抢劫居民财物。民间走私贸易因官方交易的断绝大为活跃,走私团伙规模扩大,携带武器,勾结沿海势家豪族,将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偷运到日本,赚取厚利。一些失去衣食来源的市井小民纷纷加入走私团伙,或交易或抢劫,混乱随之加剧,史称“嘉靖大倭寇”,是明代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这些倭寇并非中国与日本双方政府所能控制,因为当时日本国内藩镇割据,群龙无首,无力控制沿海武装力量。最大的几个倭寇首领,如王直、徐海等,都是中国人。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最大的“倭寇”组织王直集团大规模来袭,地方官仓皇塘报,明政府正式称其为“倭寇”,可那实际是中国人当首领、以中国人为主,有一批日本浪人依附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为行动方便,他们也乐意装扮成日本人,同时在中国沿海岛屿及日本九州一带拥有数个据点。王直绰号“老船主”,自称“净海王”,原是徽州海商,因贸易不通便以抢劫为生,流亡日本,盘踞五岛列岛为根据地,在日本平户有家,经营多年,遂成最大的海盗首领。另一方面,因为捕获“真倭”赏赐更多,明朝官兵也乐意把敌人统统虚报为倭寇。《明史·日本志》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应该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比例。但事实上所谓“真倭”才是“从倭”。
倭寇是中日历史悠久的海上贸易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力量的具体化,只不过这种具体化因为朝廷的错误政策而采取了恶性的形式。而且因为在中日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强势方,有着高额贸易顺差,对这一贸易的需求更为强烈。中国沿海的倭寇大本营双屿港——现在的舟山六横岛——甚至一度成为当时的东亚贸易中心。传统的倭寇说,完全遮蔽了中国本身对海上贸易的极度需要,遮蔽了中国人的“海洋特性”。
事实上,很少见诸中国史料文献记载,但却是一个史实的,是从宋一直延续至明清都相当猖獗的中国海盗势力。除了北部和东部沿海的倭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南中国海的海盗都是一支令人谈虎色变的力量(好莱坞电影《加勒比海盗》中对此有某种漫画化的描写),对中国海上贸易体系骚扰最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倭寇,也不是与东南亚诸小国的贸易摩擦,而就是那些称霸一方的中国海盗——宋代的香港大屿山和越南占婆,都曾是势力很大的中国海盗据点;清嘉庆年间称霸南海的“六旗联盟”,仅其中势力最大的红旗帮,就拥有1.7万人、226艘船、1315尊炮(详见穆黛安著《华南海盗》)。
倭寇最后的消失,并不是因为神话般的“戚家军”。戚继光固然战功卓著,但这种对付流寇,尤其是后台背景无限广阔的海上流寇的战争,通常是治标不治本,治得了一时治不了一世。实际上,就在戚继光用兵的同时,明政府开始逐渐放宽海禁。朝廷中一些官员意识到海禁过严,使沿海百姓失去谋生手段,“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开放海禁是彻底解决倭寇问题的唯一办法。嘉靖以后,明政府采用较为开放的政策,倭寇问题随之迎刃而解。嘉靖海禁及倭寇之灾,再好不过地从反面,检验和注释了中国“传统”中对海洋的巨大需求。
甲午
当然,甲午之战是败于北洋水师的覆灭,是中国海上力量对日本的完败。但是这只是满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之败,是满清朝廷腐朽制度之败,而不是所谓“中国传统”缺乏海洋观念之败。
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缺乏海洋观念,使得到了清末,中国稳稳占据了数千年的海上贸易中心地位被逆转,恰恰相反,是清王朝“末期综合征”使他们完全脱离民众,一意孤行地闭关锁国,完全不能体察民众对海洋的巨大需求,将自身封闭保守的既得利益美化为“传统”。中国传统排斥海洋,只是满清统治者为了使自身统治合法化而编造的神话。
甲午的真正教训其实和海洋还是陆地无关。广袤的中国大地既有连绵不绝的海岸线,又有深厚的内陆腹地;既有众多人口以海上贸易为生财之道,也有众多人口以农业、手工业为生存之本;既有海洋的利益,也有土地的利益。政府的职责是倾听民众的声音,平衡各方的利益,顺应时代的需求。而像鸦片战争以后的历代清廷那样,只知“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谭嗣同),以一种变态的心理琢磨王朝的前景和民众的心态,在恐惧和色厉内荏中越来越孤悬自闭于国内社会之上、国际社会之外,对民众“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而造成“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民力日苶,民智日卑,民德日薄”(严复)的结果,那么,理论上再好的政策,实际上也只能是一些败招。病到最深处,良药也是毒了。
无论如何,重要的不是奢谈什么从传统寻找失败的根子,而是仔细看一看,为什么甲午之后不久就发生了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什么全新的观念,人的观念和社会的观念,在甲午的冲击下得以传播,并迅速赢得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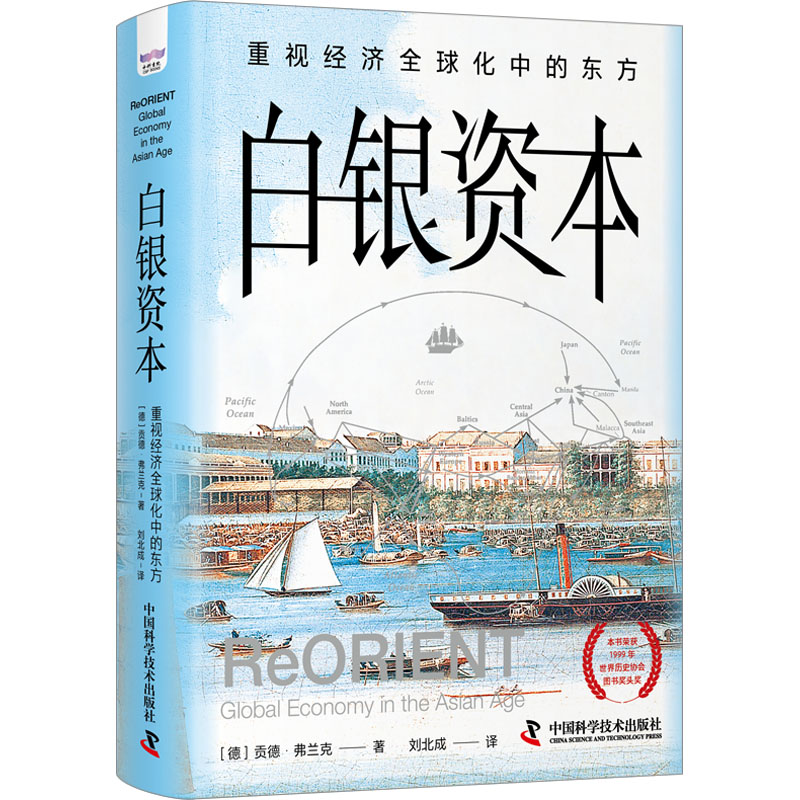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德]贡德·弗兰克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年11月版

《华南海盗,1790-1810(增订本)》
[美]穆黛安 著
商务印书馆 2019年2月版
北向资金今日净卖出48.64亿元,江淮汽车、赛力斯等获加仓
前十大成交股中,净买入额居前三的是江淮汽车、赛力斯、万华化学,分别获净买入3.83亿元、1.26亿元、0.93亿元。11月10日,北向资金全天净卖出48.64亿元,连续4日净卖出;其中沪股通净卖出33.15亿元,深股通净卖出15.49亿元。本周北向资金累计减仓近80亿元。前十大成交股中,净买入额居前三的是江淮汽车、赛力斯、万华化学,分别获净买入3.83亿元、1.26亿元、0.93亿元。锤子财富2023-11-10 18:13:070000国家能源局:5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4%
前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532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了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9%;第二产业用电量495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第三产业用电量1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8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0000WTO总干事警示:无法承受没有任何可交付成果的MC13
伊维拉认为,中国经济政策不仅可以拉动国内消费,也有助于促进全球贸易复苏。世贸组织(WTO)总干事伊维拉警示,鉴于当前全球形势,“我们无法承受没有任何可交付成果的WTO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MC13)。”“世界寄希望于WTO。为了取得成果,必须在雄心和实用主义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她在19日表示。锤子财富2023-04-20 19:16:280000政治局会议强调扩大内需,聚焦汽车、文旅、家居、电子产品赛道
对于所涉及的几大消费产业,第一财经采访了各个行业内的从业者以及专家。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4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锤子财富2023-07-24 23:26:430001上海:抓紧研究浦东新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
聚焦协同性、有效性,着力强化示范引领作用。1月26日,国新办就推进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举行发布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华源表示,此次试点方案发布,是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下一步,上海将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全力以赴抓好推进和落实。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