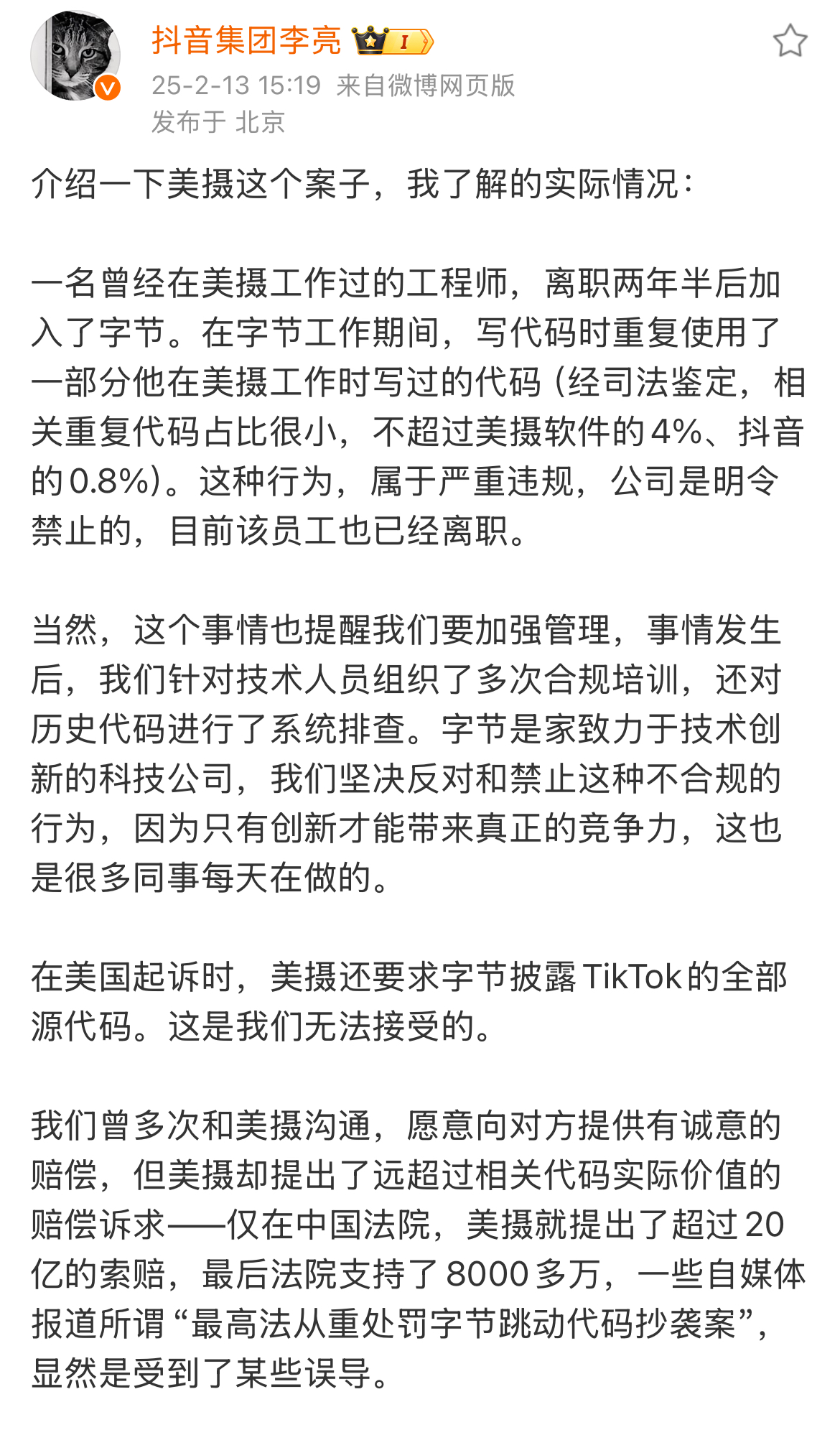顶尖大学是精心布置的迷宫,她想帮寒门子弟顺利通关
“再忍忍,上大学就解放了”,“现在高中紧,等到大学就松了”。高三学习最辛苦时,不少老师会这样安慰学生。
然而,90后青年学者郑雅君通过对北京、上海两所名牌大学毕业班62名学生的深度跟踪访谈发现,进大学后非但不能“躺平”,还要面对一场激烈又隐性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游戏规则”、能否掌握上大学的技巧。否则,进校时分数差不多的同学,毕业时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
郑雅君把大学的“游戏规则”写进《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希望“寒门学子”可以拿着她画的“地图”,在“游戏”中顺利通关。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郑雅君更想把它比成“如何上大学”的科普,“规则其实很不复杂,只是一些同学不知道,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们”。
“985废物”不知道的一些事
郑雅君如今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读博士,《金榜题名之后》脱胎于她的硕士论文,主要研究一个常见但又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为什么社会出身弱势的学生,即便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时劣势依然明显?
问题对应到现实中,就是网上很多人自称“985废物”,他们过五关斩六将,通过激烈的高考筛选升入名校,大学过得很迷茫,毕业后又很失望,觉得自己只是“小镇做题家”。
郑雅君也被类似困惑纠缠了很长时间。2009年,当她以甘肃省第40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时,还没见过地铁。和母亲分别时,只会如从小给她的许诺一样说:“妈妈,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学的!”那是她第一次遇到大学教授,对于接下来该干什么、学什么、怎样学、学了有什么用,一概不知。
选课是开启大学生活的第一把钥匙。郑雅君现在还记得,坐在机房里,翻看着那本厚达几百页、囊括几千门课的《本科生课表》,茫然又窘迫。从小习惯了所有课都由学校来安排的她,第一次听说“选课”这个概念,很难理解由学生自己来选课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选某门课?结果会是什么?“完全都是懵的”,“当时直接就懵掉了”,时隔14年,她还是用了一连串“懵”,来表达当时的感受。最自卑时,甚至想过回去重新高考,然后去一所差一点的大学提振心情。
大学里,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同学就明显不同。他们高中就读的省市级一流名校,学校课程和大学衔接得很好,也有很多选修课,进大学后,这些同学不仅很快就选好课,而且很会“选”。其间暗藏的玄机,郑雅君也是过后才明了——每门课对应的成绩,将来会换算成绩点,在某些时候决定了你是否能获得一些关键的机会和资源。选课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选”来铺设一种战略,让自己更可能获得高绩点。
在机房选课时,郑雅君从其他同学的只言片语中隐隐发现,选课是有“门道”的,但她并不知道,也不好意思主动去问那些“门道”具体是什么,“大学里有些关于‘游戏规则’和类似‘攻略’的东西,学长学姐知道,但老师在正式场合永远不会告诉你”。
大学是个精心布置的迷宫
读了硕士后,郑雅君还是难以忘怀本科时的周折和茫然。随着在教育社会学领域的耕耘,她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非个案,而是一种结构性现象,来自社会出身带来的局限的见识。她很想知道,社会出身的影响,如何延续到大学阶段,并造成同学之间的分化?
为了寻找答案,2015至2018年间,郑雅君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两所著名大学,对毕业班学生做深度访谈。她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地域、父母教育水平四个维度,把访谈对象划分为社会出身优势和劣势。根据受访者对大学生活的体验,以及她自己的切身感受,她把大学比作一个精心布置的迷宫。上大学的过程,不是中学老师说的那样无忧和舒适,而是一场挑战很高,规则也很复杂的探险之旅,需要探险者有领悟力,早点认清迷宫的地形,尽早决定自己要去哪个出口,适时调整线路,才能顺利抵达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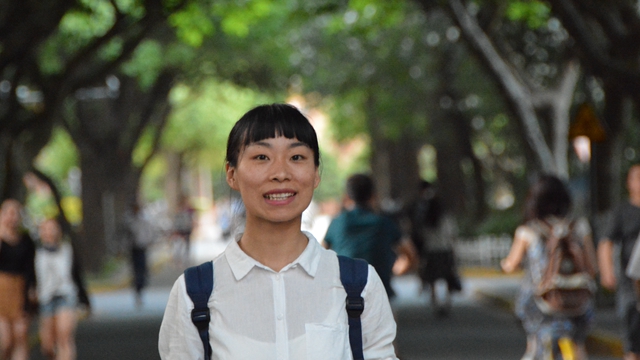
访谈前,郑雅君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是他们有意主动选择的结果。随着对方向她敞开心扉,她发现很多人并非如此,只是在全无计划的情形下,临时抓住一个恰好够得着的机会。这个发现也与之前学者的研究对应上了——弱势家庭学生的就业结果不及优势家庭。
最需要工作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尽早做职业规划?郑雅君发现,学生参与大学生活的模式,可以粗略分为“直觉依赖模式”和“目标掌控模式”。“直觉依赖模式”也就是俗称的“习惯性优秀”——在没有任何具体目标的情况下习惯性保持优秀,这些学生不了解游戏规则,仅凭感觉在“迷宫”里摸索,甚至走了很多弯路。他们基本都来自社会出身弱势的家庭。
而家庭条件更优越的学生,基本属于“目标掌控模式”,从进校开始,仿佛就有一张“迷宫”地图,他们看得清迷宫的全貌,知道如何闯关,会预先制定路线,最后获得丰厚的游戏奖励——稀缺的好工作或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郑雅君认为,大学生出路分化背后,与他们是否了解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密切相关。但是,这些“游戏规则”又与家庭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难以在课堂上学到。而当今大学的评判标准,以及职业竞争的游戏规则,客观上都有利于“目标掌控者”。“小镇做题家”就算进入顶尖大学,也是弱势群体,被这些文化障碍困扰,不知怎么做才能抓住机会。
人和人真的差距可以这么大
一位家境优越,家里父母、祖父母都受了很好教育的“目标掌控型”男生,和郑雅君谈了6个小时,说自己如何设计大学四年的目标、达成目标,如何求职。“和他聊天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也真的会陷入沉默。他的生活和我的真的完全不同。”
郑雅君印象很深的是,这位男生学习优秀又轻松,但他觉得,成绩好只是一条及格线,自己还有很多别的目标和兴趣,学习好只能证明智商正常。“对我来说,这些话听起来都是在碾压。”郑雅君苦笑着说。
因为对“迷宫”游戏规则很熟悉,自己也目标明确做了准备和努力,毕业时,他轻松拿到很多知名公司的面试机会,比如花旗银行、麦肯锡、摩根大通、国内四大银行等。他都去面试了,还给郑雅君总结不同公司的面试规则,“你知道吗,他是真的在玩,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还可以抱着这样的心境去参加面试,去找工作。”最后他选了个薪水过得去,但有一定自由时间的工作。
来自湖南农村的冰倩(化名),一路走来经历的坎坷,同样令郑雅君难忘。她是家里老大,很小父母就外出打工,后来又离婚。高一时,冰倩因为种种原因不想上学,一度辍学到广州打工。几个月后她后悔了,经过很多波折和努力,终于复学,在功课落下整整一学期的情况下拼命学习,两年后考进上海的名牌大学。
从小,冰倩的奶奶就说,考上大学就有出息了。可是来到大学之后,她不知道怎样才是“出息”。她也经历了郑雅君有过的无助、茫然、自卑,但与郑雅君的努力被系里老师看到、认可不同,冰倩拼尽全力学习,专业课老师给的分数还是很低。系里很多出国、出境交流的机会,她碍于英语口语不好,也不敢申请。
毕业时,冰倩在辅导员的鼓励下,努力实习,在上海找到一份月薪8000元的工作。这时,外公外婆生病了,父母离婚后老人无人照看,她最后决定回老家工作。
访谈得越多,郑雅君越感慨,“你会发现,人和人的生活真的差距可以这么大”。冰倩的故事尤其让人唏嘘。“你真的能感觉到弱势家庭出身的人,大学里的努力要兑换成好的前途,会受多重障碍的影响,打很多折扣。家境更好的同学,他们的努力不是被打折,而是被‘加成’,同学之间的差距就拉大了。”
研究也是一种自我治愈
在国内学术评价体系中,学术著作的分量比不上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年多前,郑雅君在导师的鼓励下,顾不上自己尚在哺乳期,襁褓里的儿子也没人带,硬是利用碎片化时间,一点点为出版做准备。“我明明看到有些人因为不知道那些被默认的规则,而失去很多机会。不把自己知道的写出来,会于心有愧。他们真的是吃尽了苦头,才能来到这里。”
《金榜题名之后》的研究,对郑雅君来说也是一种治愈。她是甘肃张掖人,父母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双双通过高考跳出农村,在地方上有不错的社会地位。除了父亲不幸在她11岁时早逝,成长环境顺遂,从小到大成绩也很好。
可到了上海后她备受冲击,在学校不适应各种“游戏规则”,面临文化障碍,乘坐出租车时,司机一听来自甘肃,脱口而出就是“你们那里很穷,是不是不洗澡?”很长一段时间,自尊的她都羞于谈及家乡,“我觉得好像很丢脸,把自己看得很低,嫌弃自己”。
访谈、写作和出书的过程,前后时间跨度很长,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后来结婚,当了母亲,“这个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命,从很多人的叙述当中,体会到了生活和社会的重量”。郑雅君说,虽然自己小时候有段时间在农村长大,对农村生活的艰辛有一定了解,但以前没有真正体会到社会对人的结构性束缚。她开始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里写的那样,反思自己的身份与作为研究者的角色。“我和访谈者也有很多讨论,不觉得做‘小镇做题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大家并不想要停在这儿,说世界真的好不公平。也有人会非常坦荡地接受自己的过去,和过去和解,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
郑雅君还说,可喜的是,近年来“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被学术界指出后,在公共层面引发很大触动,国家在高考环节采取了很多努力,重点高校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实施招生专项计划,很多大学也建立起对弱势学生的支持体系。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
郑雅君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月版
——————————————————————
对话郑雅君:我研究的不是教育,而是每个家庭的希望
教育是社会希望的引擎
第一财经:你现在读博士的研究方向与教育公平有关,为什么会对这个方向产生兴趣?教育公平说了这么多年,还能在哪些领域有新的建树?
郑雅君:我经常觉得我研究的不是教育,是每个家庭的希望。教育在全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承载了家长对子女未来的美好想象,包括我家也是这样,从小我要是羡慕谁或者喜欢什么东西,我妈就会说,“好好学习,以后你想要的东西就会有”。可以说,教育是社会“希望的引擎”,所以全世界都在说教育公平,因为不管是什么阶层,有孩子后,都希望孩子可以收获一个丰盛的人生,这些都得靠教育去实现,教育公平就很重要。
的确,教育公平说了很多年,实际上没有真正实现,只是在量上有所平衡。而且教育公平说起来好像也没什么新意,可是一旦遇到现实教育中的每个环节,比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包括跟教育衔接的部门,比如劳动力市场、教育培训、家庭教养等,能把经验事实描述清楚、讲清来龙去脉的研究还是比较少,我们对于教育不公平背后的机制、发生原理的理解也远远不够,结果就是有些政策本来是想实现教育公平,却导致了更加不公平的后果。

第一财经:很多从小地方考到大城市的60后、70后、80后,进大学时都经历了无助、自卑、迷茫,靠你总结的“直觉依赖模式”摸索。我看了《金榜题名之后》,很意外的是这些经历,在社会出身弱势的90后身上依然存在。90后成长的时候国家经济已经在高速发展,整体而言父母接受的教育也比之前几代人更多,为什么他们面临的文化障碍,相隔几十年还是没有变化?
郑雅君:其实90后面临的文化障碍,与以前相比更大。原因是,80后、70后、60后上大学时,整个社会分层没有那么大,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差异也没那么明显,各群体还没有形成明显的文化上的区隔。一个表现是,70后、80后还能共享童年。90后不一样,他们生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从小就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分层,很多同龄人已经不共享同一种童年了。
另外,进大学永远是要筛选的,名牌大学筛选程度就更大。很多研究已经表明,大学扩招其实没有导致平等化,只是把阶层竞争推高到了重点高校层面,也就是说,名校更多吸纳了家庭条件好的学生,而低阶层学生在校园里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而大学的游戏规则和非正式文化,往往是由条件更好的多数群体定义的,很多规则都是他们所默认的“常识”,比如你一进来就知道怎么选课,至少知道应该规划你的大学生活,这些低阶层的大学生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就很不适应。
道德批判是弱者的抵抗
第一财经:你做访谈的时间是2015至2018年,当时的国内外大环境都比现在好,所以哪怕有些学生没有太多目标,因为有名校光环,最后还是找到了旁人看来不错的工作。但是这几年形势完全不一样了,大学生找工作、出国、考研、考公都竞争非常激烈。要是现在做访谈,社会出身优势和弱势的学生,毕业时的差距和之前相比会有变化吧?
郑雅君:差距肯定是更加扩大。以前我访谈时,30%的人出国,30%的人工作,剩下的基本都保研了,那时周围很少有人考研。实在保不了研,也能做选调生。当时,除了江浙沪之类的东部地区选调生比较热门,其余内陆省份的选调生,对名校学生来说基本没有门槛,他们还有个保底的“安全网”。现在不是这样,原本想出国的学生寻求保研,原本能保研的学生可能需要去考研,本来人少的选调生赛道都开始“卷”。经济下行,肯定就有一部分人被挤下船,弱者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更厉害了。
第一财经:我在读《金榜题名之后》《寒门子弟上大学》《“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这几本书时,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身底层家庭的学生普遍不善于社交,很多人还把善于交际当成是“拍马屁”。就像你访谈的那些“直觉依赖者”,普遍对实现目标这个行为有道德批评,认为“目标性强”。为什么普遍会有这种现象?
郑雅君: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写过《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讲人们免不了去做道德评判,而且往往从不同的出发点去批判,认为这是“人心的一种癌症”。低阶层的人会倾向于和优势阶层划定一个道德边界,彰显自身的道德价值,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是有普遍性的。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Lamont)在《工作者的尊严》(TheDignityofWorkingMen)一书中说,工人阶级相信,他们的道德价值是中产阶级和高阶层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特别勤恳,赚自己的劳动所得,很正直,这些是他们认为自己价值的很重要的来源。在加拿大、英国也有研究发现了类似现象。
从我的角度说,如何理解这种现象?我觉得可能是身为弱者的一种抵抗,通过在道德上建立优势来对抗自己的弱势地位、弥补自己的低自尊。所以他们通常会说,那些“目标掌控者”投机取巧,破坏规则,而他们至少保留着淳朴与正直。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前面所说的,读书这件事情对低阶层的人来说,寄托着整个家庭对明天的指望,底层离大学场域太远了,就容易将其神圣化。学校规则在他们心中是神圣不能侵犯的,也是不能利用的。当他们看到另一些人居然可以这样利用规则,会有内心的神圣性被亵渎的感觉。
优势家庭的学生完全不同。他们的父母可能本来就是大学老师、干部或其他专业人士,大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近”的地方,心理上没有距离,自然不会产生神圣感。他们往往是带着吐槽的、蔑视的、审视的、批判的态度去看待大学这套游戏规则。
同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第一财经: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里说:“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你访谈的那些“目标掌控模式”的学生,他们做事理性、目的性很强,成功可能性当然更大。但会不会长期处在这种习惯性“规划”和“成功”中,不自觉地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了这么多访谈后,你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怎么看?
郑雅君:确实很多人有这种倾向,他们没有确定的价值目标,但是很知道利用游戏规则,也能看到机会,哪里能让他们成功,就往哪去。访谈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会提到他们身边有这种现象,特别是那些低阶层的“直觉依赖者”,会用鄙夷的口吻说自己身边有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就看不上那些人”“我不想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但是,我并不同意抨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从道德的角度去批判他们。它既已成为一个现象,就说明背后是有社会性原因的。据我观察,很多可以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同学,是有想追求的东西,有社会理想的。他们后来之所以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因为早早认清了当下环境没有条件让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新闻系的学生,抱着新闻理想来读大学,但毕业恰好很多纸媒关闭,对行业冲击特别大。他说,反正都是“当狗”,不如找块“有肉的骨头”,就去了金融行业。我能感觉到,这条路本不是他想要的,但他很无奈,因为他要承担生活的重量。
还有一个同学是教授家庭长大的,学政治学专业,很有社会关怀。他说,自己没什么物质欲望,不需要挣那么多钱,家里也不缺钱,就想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再为社会做些事情。我绝对相信他是真心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们在一个非常喧嚣的茶餐厅里,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都在发亮。可是前两天我联系他,他说在“卷”金融、赚钱。转折点是工作时碰到了一个非常“卷”的老板,他妈又让他背上了北京的房贷,现在他每天都怀疑自己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社会造就的,这一代的父母也非常实用主义。社会对成功的评判标准就是这样,让他们怎么办?这些同学也想离开所谓“精致利己”这条路,但你得问问父母同不同意,社会怎么看。所以,这归根到底是社会的评价文化的问题。我对这些同学抱有非常深的同情,批评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公正的。何况现在的社会环境中,很多骂他们的人,如果有了他们的条件,我相信一样会成为“精致利己”的人。
未来还将继续跟踪访谈
第一财经:未来你是否还会长期关注这些访谈者的发展和变化,让研究时间跨度更长,研究结果呈现更多层次?
郑雅君:如果我的生活没有大变故,哪怕没有项目支持,我都计划每10年回访他们一次,可以追他们一辈子,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前两天我因为寄书联系上他们,他们都很高兴,也很有兴趣今后继续参与我的访谈。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跟《人世间》里的周秉义差不多,通过高考实现了向上流动,到一个新的阶层,今后肯定还会遇到很多问题。随着大家生活境遇的变化,我们也可以探讨些更深的东西。
我现在写的博士论文里,已经开始讨论人们如何化解这些文化障碍。我目前觉得,要化解文化障碍,至少分为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个体层面一是不断尝试,同时意识到你所经历的不适应是一种正常的、结构性的现象而不是你的错。二是自我协商,追问自己,如何安放自己过去的身份。虽然我们很强烈地被社会的声音所影响,可你是自己的主人,自己仍然保有一定的自由度,也可以拒绝社会给你的声音。借鉴一些古老的智慧或者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把心结解开,这是一个自我协商的过程。
从社会层面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应该意识到,或者去反思,社会提供的价值判断不能单一,比如用赚多少钱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而是应该迈向对个人的价值定义更加多元的社会。我们需要多织几张“意义之网”,让人们可以把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挂上去。这是一个复杂的、牵涉多方的文化转型工程。教育界、媒体界、学术界、政策制定者都有自己可做的一份。当我们的孩子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不用仅仅建立在考分和收入这些绩效指标上,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文化有更多认同,也会有自信去“平视”那些与自己不同的文化。
我非常期待我以后的访谈,希望可以把他们与自己和解的故事讲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挣扎,从他们的解决之道中获得启发。其实我观察下来,不管人先天禀赋有多好,不管出身什么家庭,只要是社会人,都会承受结构性的束缚,都有自己的困扰,只是这些困扰在不同群体呈现为不同样貌,所以也没必要过度美化中产阶层的生活。
AI迎来全球管控时代,但马斯克的“第三方裁判”靠谱吗?
《宣言》尤其关注网络安全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风险,以及前沿AI可能放大虚假信息等风险。全球在人工智能风险监管方面的步伐在加快。锤子财富2023-11-02 22:59:560000权益基金“锁”3年仍难赚钱,基民发愁:“亏本也赎回”
“梦想与实际仍有差距”近年来,为引导投资者长期投资,减少“追涨杀跌”行为,带持有期的基金产品不断涌现。但据记者观察,因业绩不佳,部分投资者的体验感并不如预期。随着不少“三年期”主动权益类基金产品陆续届满,业绩表现和持有体验也引起了市场讨论。锤子财富2023-05-25 19:39:330000微软再次出手“囤电”,人工智能掀起核能发展新浪潮?
瑞穗预计,2030年人工智能等耗电量将超过英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巨大的用电量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上周微软公司宣布,与星座能源公司(ConstellationEnergy)达成协议,购买三里岛核电站未来20年内的电能。在绿色经济和气候问题等因素推动清洁能源的强劲需求下,全球正在推动本世纪中期大量新建核电项目落地,科技巨头的加入有望让核能的发展获得更多动力。科技巨头积极寻电锤子财富2024-10-07 14:30:400000上海出台住房公积金支持城市更新政策 10月7日起正式实施
《关于本市住房公积金支持城市更新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对纳入本市城市更新范围内的旧住房更新改造项目实施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为支持深化城市有机更新,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提升居民居住品质、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制度作用,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六十九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本市住房公积金购买存量住房最长贷款期限的通知》及《关于本市住房公积金支持城市更新有关政策的通知》。0000公司将回归华为?荣耀CEO赵明回应;“花西子公关部或集体离职”?知情人士回应 ;恒大地产新增7条被执行人信息丨大公司动态
第一财经每日精选最热门大公司动态,点击「听新闻」,一键收听。【科技圈】公司将回归华为?荣耀CEO赵明辟谣:绝无可能、期待竞争9月19日晚间,针对荣耀将回归华为的传闻,荣耀CEO赵明做出辟谣。他表示,荣耀回归华为绝无可能。“华为是其最尊敬和最期待的对手,荣耀要把自己变成华为合格、优秀的竞争对手。”孟晚舟:华为支持每个组织使用自己的数据训练出自己的大模型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