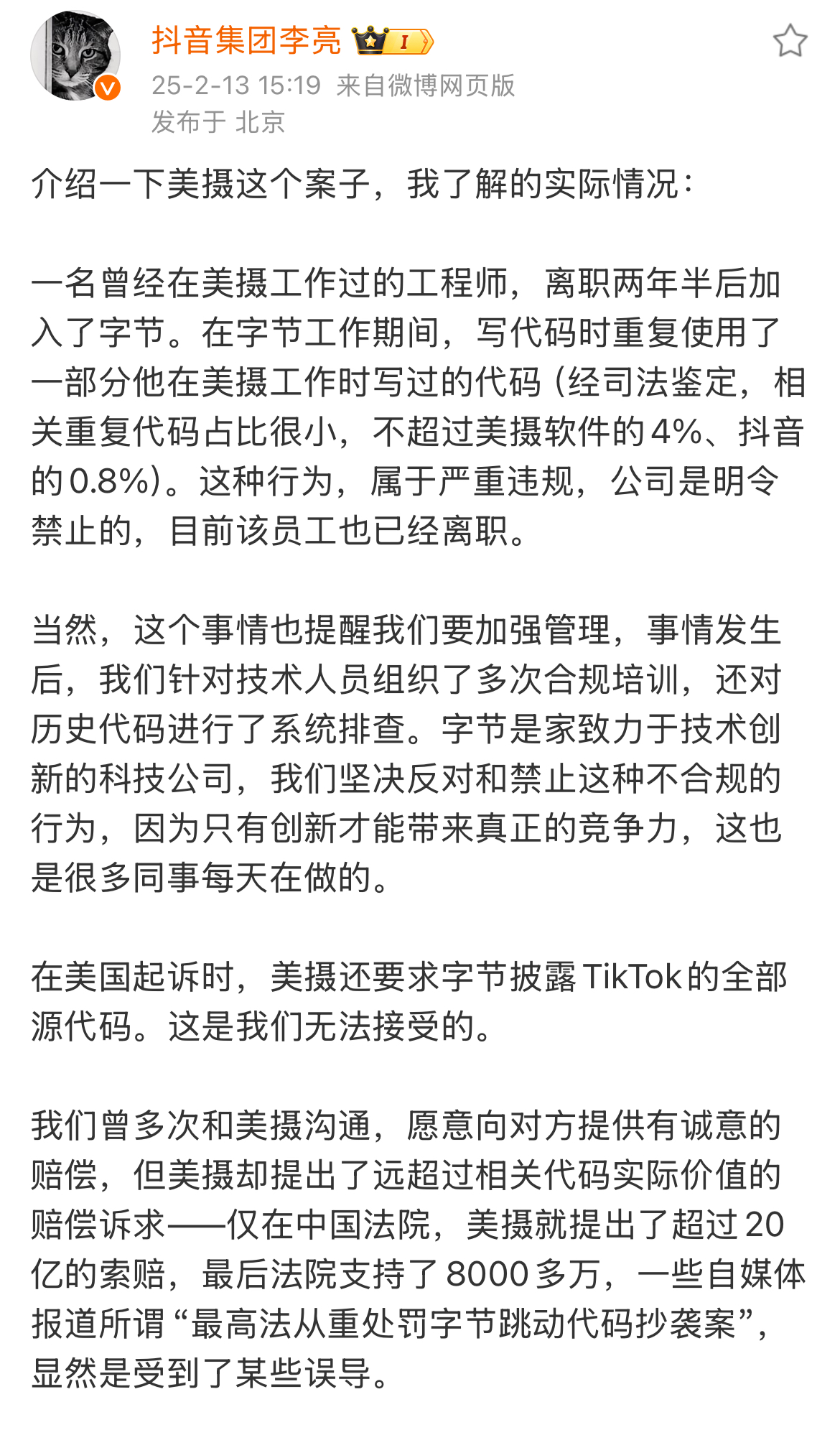重读聂鲁达:独一档的抒情与自恋
电影《邮差》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影片之一,叙述的是智利大诗人聂鲁达在岛上避居时,教一个害羞的男青年学写情诗,送给自己的心上人。
片中的聂鲁达形象,使人过目难忘:他肥胖,眼皮低垂,说话迟缓,一般情况下都是冷淡的,一旦念起诗文,或是搂着情人马蒂尔德慢悠悠地跳舞,他的热情就会从肉身上很有限的几个出口,嗤嗤作响地冒了出来。

聂鲁达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早就“候选”多年,说他大器早成、名满天下是毫不夸张的。他的几部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大地上的居所》《漫歌》《元素颂歌》等,就风格而论是“独一档的存在”,而且不像很多伟大诗人的诗作那样,吸引人去分析,去玩味。他的诗常常纯是一种汹涌的情感倾泻,犹如一只心脏起搏器,用近乎物理的方式摇撼人心。
我们甚至遗失了暮色。
没有人看见我们今晚手牵手而蓝色的夜落在世上。
我从窗口看到远处山巅日落的盛会。
有时一片太阳像硬币在我手中燃烧。
我记得你,我的心灵攥在你熟知的悲伤里。
你那时在哪里?
还有谁在?
说了什么?
为什么整个爱情突然降临正当我悲伤,感到你在远方?
摔落了总在暮色中摊开的书本我的披肩卷在脚边,像只打伤的狗。
永远,永远,你退入夜晚向着暮色抹去雕像的地方。
这样的诗简直是以霸道的方式,决定了读它的感受和方法。不过,一旦在一位作家的作品面前觉察出作者的性格、他的态度和“倾向”,阅读心得就会进入了另一条轨道。今年7月,时值聂鲁达120岁冥诞,我不由回思起,自己一度多么讨厌他的自恋。
1973年9月中旬,聂鲁达完成了自传,11天后他就去世了,死因一直存疑,因为就在9月11日,智利第一位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被政变军队杀害,身为阿连德的挚友,聂鲁达紧随其后也走了,难免要引人疑问,毕竟拉丁美洲各国军阀政治的黑暗是臭大街的。他的自传的中译本,最早的书名译作《我曾历尽沧桑》,往日读这本书,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确只能在书中看到作者的主角光环。聂鲁达漫游世界各地,少数时候化险为夷,多数时候都会遇到狂热的崇拜者,穷困、孤独,全都是他赖以突出自己的手段,没有哪一页里,看不到被反复强化的“我”。
就说书中的两个故事。第一个的发生地点是上海。
在拉美,成名的文人、知识分子往往会从政,像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人巴尔加斯·略萨,以及墨西哥人帕斯,都是如此。聂鲁达在1927年被政府委任去做驻外使节。外交部给了他几个选择,他随随便便就选了缅甸首都仰光,去那里当领事。这条赴任之路相当于一次欧亚漫游,那年6月,他坐船斜渡大西洋,到葡萄牙里斯本上岸,然后分别到过西班牙马德里、法国巴黎和马赛,接着来到上海,之后还要去新加坡,在那里坐好几天的船才能抵达仰光。
在1927年的上海,聂鲁达有怎样的体验?“名声不好的城市就像致命的女人一样吸引着你,”他写道,“上海为我们这两个漂泊在外的乡下男孩张开了它的夜之大口。”他和同伴阿尔瓦罗去了一家一家夜总会,那是一些“罪恶和迷失灵魂的窝点”,“在那里我们正在失去的只是时间”。
那时的聂鲁达才23岁。回去时,他叫了人力车。开始下雨了,雨越下越大。这时细节出现了:人力车夫体贴地停下马车,小心翼翼地用防雨布盖住车头,不让一滴雨水溅到他俩的鼻子上。聂鲁达写道:“他们真是一个高雅又体贴的民族。两千年的文化没有白费。”
但接下来情况起了变化:很快,黄包车夫赤脚奔跑的声音,和其他赤脚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有节奏地小跑的声音一起响了起来,渐渐地声音变小了。“这表明人行道已经到头了。显然,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城外的开阔地上。”
黄包车突然停了,车夫熟练地解开为客人遮雨的布篷,外边是荒郊野外,聂鲁达和阿尔瓦罗爬下车,七八个中国人围拢来,伸出手,嘴里喊着“钱!钱!钱!”阿尔瓦罗想要掏武器,却挨了一拳,聂鲁达也挨了一拳,但中国人却在半空中抓住了他,使他没有摔倒,而是轻轻地被放在了湿地上。
聂鲁达把这次历险写成了异域风情的一部分。我能肯定,不会有什么研究上海民国史的史家,会把他写的这个故事当成可以引证的史料,诗人的话毕竟当不得真,可是诗人对情景的勾画又实在是大师级的,他只用寥寥数语,写自己坐车时听到的声音,就使读者看到一个人力车夫在雨夜狂奔的场景。接着,车夫和他的同伴现出了本相:
“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遍了我的口袋、衬衫、帽子、鞋袜和领带,就像变戏法的艺人在展示高超的技艺。我们身上的衣服一寸不剩,我们仅有的一点钱一分不剩。但有一点:他们秉承了上海小偷的传统,对我们的证件和护照慎之又慎。”
这次遭劫真可称“完美”,不免使人觉得,有神灵在保护大诗人,用最凶险的经历来为他增加传奇色彩,又让他安然脱险,好让他日后能绘声绘色地写下它。不管怎么说,上海小偷的恪守行规,确保了聂鲁达得以保持他高昂的劲头,继续他的旅程。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2年。那时聂鲁达从西班牙内战后的流亡中回到智利。在首都圣地亚哥,他又一次上了不明身份的人的车,再一次被穷苦人围在中间。但这次,车开到的不是月黑风高的抢掠场,而是另一群赤脚汉的聚居地:圣地亚哥中央集市,工会组织的活动大厅。
集市里穷得穿不起鞋的工人,聚在破旧的大厅里等待着他们的偶像。大约有50人,坐在板条箱或简易木凳上,有些人腰间系着像围裙一样的麻袋,有些人则用打满补丁的旧内衣遮住身体。还有一些人,在智利7月的严寒(智利在南半球)中光着上身。聂鲁达在一张小桌后坐下,他写道:“他们都用我的国家的人民那双定定的、煤黑色的眼睛看着我。”
聂鲁达的口袋里装了一本《西班牙在我心中》。这是他为西班牙内战而写的政治诗。这些面部肌肉纹丝不动、眼睛却紧紧盯着诗人的人,引起了聂鲁达的敬意。他拿出诗集来:此刻的心理活动是:“我该如何应对这些听众?我可以向他们讲些什么?我生活中的哪些事情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我拿不定主意。”
他读了一首,然后又是一首,一首连着一首。他没有想到,这些缺少文化、眼界闭塞的工人,会对诗中写的发生在大西洋对岸的事情如此感兴趣。当聂鲁达站起来,准备谢幕时,“一个人站了起来。他是那些腰上腰间系着麻袋的人之一。他说:‘我也想告诉你,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如此感动,我们从未如此感动过’”。
但这个故事却不能打动我,仅仅因为我不喜欢其中的自恋。在叙说人民对他的崇拜时,聂鲁达总是不遗余力。他看着那些眼睛和黑眉毛,如此专注地追随着诗句,他说:“我意识到我的书正在击中目标……我被自己读诗的声音所感染,我的诗和那些被遗弃的灵魂紧紧相连。”有文化抱负、有写作理想的人,都苦于自己不被看见、不被听见,但聂鲁达何德何能,竟在人民的掌声面前盛情推却。
不认识他的人也对他手下留情,认出他的人则无不给予他掌声。在智利最大的煤矿——洛塔,炽热的硝石矿层上,一个男子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带着一张脱形的脸,一双被灰尘熏红的眼睛,把一只粗糙的大手(“手上的皱纹形似大草原的地图”)伸向诗人:“兄弟,我早就认识你了。”在一家舞厅,聂鲁达斥责了两名斗殴的男子,其中一人拦住了他,他以为要挨打,谁知这人涕泪涟涟地说:“我和他的未婚妻,就是因为一道背诵你的诗才相爱的。他随即拿出了未婚妻的相片,希望聂鲁达亲手拿一下。”
拥戴聂鲁达的穷苦百姓不限于智利、阿根廷和西班牙。二战之后,他应邀去苏联参加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活动,1951年他又从苏联来到中国参加和平大会,把列宁和平奖章授予宋庆龄女士,苏联人和中国人都喜欢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脸上的微笑令他难忘。除此之外,这期间的高光时刻发生在意大利。在罗马火车站,聂鲁达只是转车而已,可车尚未停稳,就见车厢外涌来了众多欢迎他的人:鲜花举过了头顶,诗人的名字被喊上了天际,人们叫着“聂鲁达留在罗马!”“聂鲁达不要离开意大利!”“让诗人留下!”
几天后,他又被安排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岛——卡普里岛上住一段时间,岛上人民的一贫如洗同醉人的自然风光的组合,完美地勾起了聂鲁达对智利家乡的回忆。那是他领受诗人天使的地方和时刻,他记得的全是自然界的奇观:连月不断的大雨,地震,火山爆发,大海的浪涛轰天而至又滔滔不绝地退走。在卡普里岛上,聂鲁达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一段创作时光:他虽孤独,却有长期的情人马蒂尔德相伴,他手头拮据,却与“世上最淳朴的人民”朝夕见面。这段卡普里岛小住,日后就成为电影《邮差》的题材来源,写故事原著的是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电影则众望所归地获得了奥斯卡奖。
主角光环紧紧箍着他。聂鲁达的回忆录,几乎不容许读者对他有别的理解。他的横空出世,就意味着诗的胜利,他的写作,他的诗的流传和他本人的漫游,就是一首首团结、自由、斗争的赞歌。
人民因为他的诗而团结起来,而世界上的那些文学同行,与他也是同气相求。西班牙“二七年一代”的诸多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塞尔努达、阿尔维蒂、阿莱克桑德雷,都是他的朋友,对后来获得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比桑特·阿莱克桑德雷,聂鲁达只给了一个词的评语:“无限多维”。法国的左派作家和诗人——艾吕雅、阿拉贡、勒韦尔迪,他不断地称誉他们的艺术,讴歌与他们的友情。至于苏联,这个反法西斯战争之后被世界瞩目的“红色首善之区”就更不用说了。他写到,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经问他:“你的诗中为什么写了这么多的根?”
真是个够诗人大大发挥一番的好问题。为什么?聂鲁达的回答就像是诗朗诵:
“的确,边疆地区在我的诗歌里扎下了根,这些根一直无法拔出。我的生命是一次漫长的朝圣之旅,它总是在自我反转,总是回到南方的森林,回到迷失在我体内的森林。在那里,巨大的树木有时会被它们700年强大的生命力砍倒,被风暴连根拔起,被大雪摧残,或被大火烧毁。我曾听到森林深处泰坦尼克号般的大树轰然倒下的声音:橡树带着灭顶之灾的闷响扑倒在地,仿佛用巨手捶打着大地的大门,请求埋葬。但树根却被露天放置,暴露在时间这个敌人面前,暴露在潮湿和地衣面前,暴露在一次又一次的毁灭面前。最美丽的莫过于那些受伤或烧伤的张开的大手,当我们在林间小道上遇到它们时,它们会告诉我们埋在地下的树的秘密,滋养树叶的奥秘,以及植物王国深处的肌肉。它们悲惨而蓬乱,却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美感:它们是大地深处塑造的雕塑——大自然的秘密杰作。”
这些话,过去我是没心思去细看的。倘若一个人自恋到了动辄自我感动的地步,他又能讲出什么有见地的话来呢?倘若他总在叙述自己的得道多助,普天下都是等待他的崇拜者,那他的故事又凭什么值得我去共鸣?
过了不少年,为了做一个讲书节目,我再次打开聂鲁达的回忆录。这番重读,我读到了一些之前忽略了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位诗人并非政治幼稚者,满足于做个国内外左翼运动的吉祥物。
人民对他个人的拥戴,他固然十分陶醉,但是,人民的无能甚至“背叛”,他也不讳言。1970年,左派终于胜选,阿连德上台执政,三年后的9月11日身死总统府,对此,聂鲁达第一没有控诉反动派谋杀了他,第二也没有为革命的失败大发恸词;有了西班牙内战的经验,他理智地讲,阿连德之死,是一系列错误的合力造成的: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阿连德低估了反动派的力量,而支持他的人民,因为没能得到及时的组织,而没有起来保卫他,使阿连德只能独自坐镇总统府,用手枪抵抗凶恶地扑上来的政变士兵。
回忆录是他个人风格的延伸,这种风格就是昂扬的,是事事处处都要回到“我”的,没有它,也就不成其为聂鲁达。我意识到,在为数不多的可称“不朽”的文学家里,聂鲁达其实是很少有人去谈论的——因为真没什么好谈。评价他的自恋,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他就在那里,像一尊弹药不竭的火炮一样不断地喷泻出诗文,那些诗句仅仅作为诗句本身,无需借助立场,无需借助其维护和捍卫的理念,就使人自然而然地仰头注视。
这就是聂鲁达“独一档的存在”的证明。我们知道,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是“反抒情”的,可是他会去批评聂鲁达吗?我想是不会的。
聂鲁达是例外,他居于那种可以被针砭、被反对的抒情之上。当爱伦堡问他,为何总爱写“根”时,他打开了抒情的洪流,其中滚滚而出的,是那些在他的诗之沸锅里无数遍翻腾过的记忆里的东西:雄伟的森林与大树,和摧毁它们的更雄伟的风暴、雪和大火,树在倒地时威风凛凛地捶打大地,并献出树根,进入被时间所毁灭的雄伟的过程。如果一个诗人,能在自然界的力量中处处看到雄伟,并把它用千变万化的方式诉诸文字表达,那么,他的“起范儿”的癖好,他的自戴主角光环的习性,就都可以谅解了吧。
谨以此文纪念聂鲁达诞辰120周年。
叶飞操纵股价案正式落幕,获刑三年并处罚金50万
对资本市场参与各方影响巨大时隔两年多,叶飞案正式落幕。近日,青岛中院发布一批证券期货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例为网络大V叶某伙同他人炒作操纵证券市场案。从监管此前披露的有关情况来看,该案中的叶某即为叶飞。0000机构今日买入这13股,抛售江淮汽车2.71亿元丨龙虎榜
当天机构净买入前三的股票分别是水晶光电、普利制药、三态股份,净买入金额分别是9349万元、6064万元、5023万元。盘后数据显示,10月30日龙虎榜中,共37只个股出现了机构的身影,有13只股票呈现机构净买入,24只股票呈现机构净卖出。当天机构净买入前三的股票分别是水晶光电、普利制药、三态股份,净买入金额分别是9349万元、6064万元、5023万元。锤子财富2023-10-30 18:14:550000逐鹿直播电商,拉动仓储需求,推进降本增效
不同形态的直播电商产生了多元化的仓储物流需求,有望助力提高现代物流规模化、网络化、组织化、集约化发展水平,进一步降低社会物流成本。刚刚过去的“618”购物节,见证了消费场景的稳步拓展、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提振消费政策的提速生效、线上平台和线下商业体的联动发力,消费市场信心与活力的回归,以及消费复苏对国民经济链条的带动作用。0000未成年人涉网合法权益保障需要社会共治
中国未成年人玩家数量、上网时长以及占比必然让中国企业成为网络治理的重要样本。探索未成年人涉网合法权益保障,是全球网络治理共同面临的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出台,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如何保护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未成年人,并为此贡献中国经验。立法脉络0000航天软件将赴科创板上市:信创核心标的、国产大型关系型数据库第一股、工业软件产品“国家队”
航天软件(688562.SH)科创板IPO申请近期获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航天软件是航天科技集团控股63.81%的大型专业软件与信息化服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是国务院国资委“双百行动”综合改革、国家发改委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