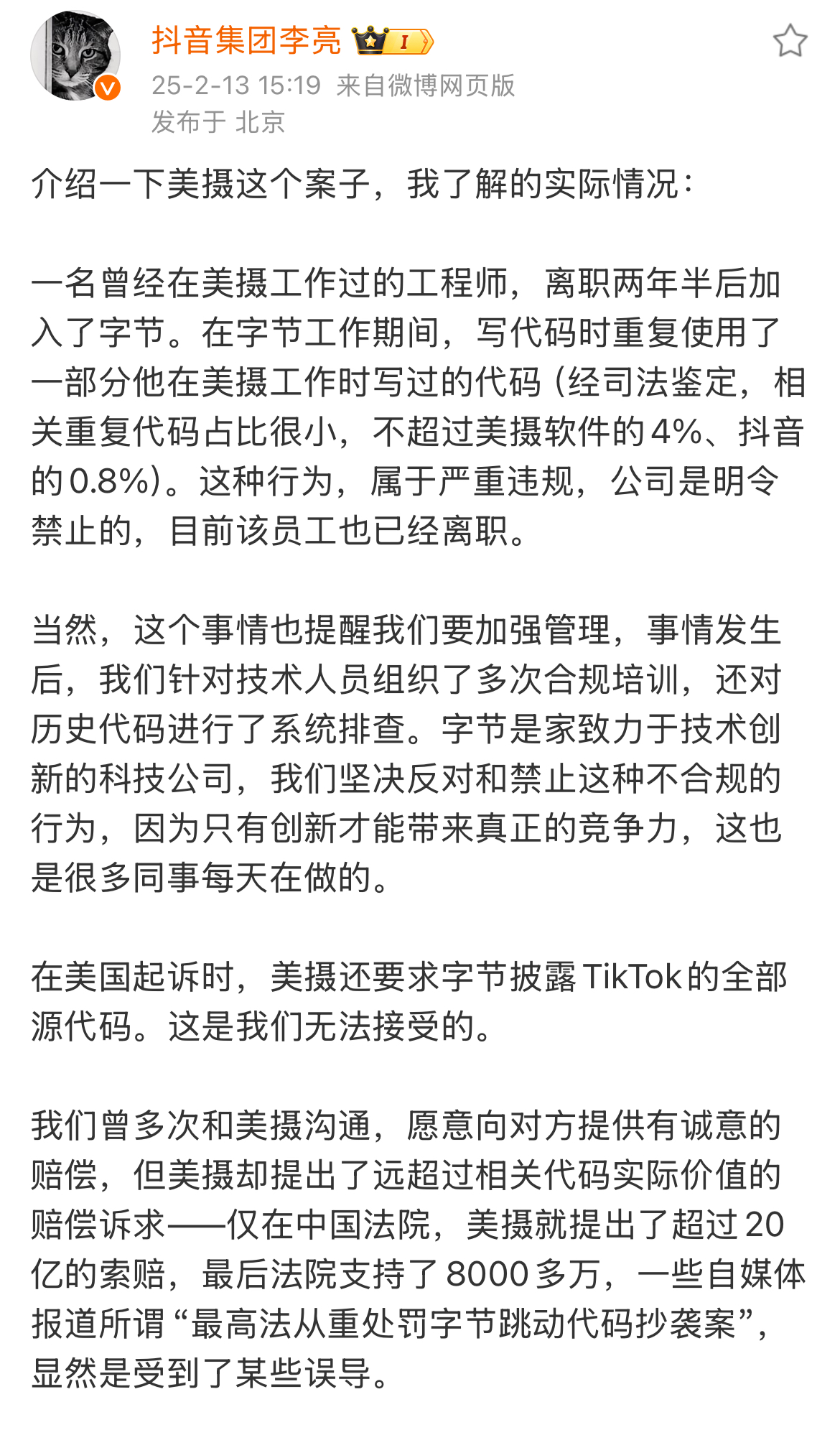犹太人、反媚俗和世界主义——纪念米兰·昆德拉
有多少成名作家,都接受过音乐的童子功训练,米兰·昆德拉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是按音乐家的标准来培养他的;昆德拉说,父亲最大的梦想就是打造一台完美无瑕的音乐会,他也用同等的严苛来对待儿子,禁止儿子的即兴发挥,或是陶醉于浅薄的趣味。结果就是,昆德拉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同时在他引人注目的小说和文论中,时不时地展现他的音乐情结和所受的审美影响。

一则音乐故事中的轻与重
在文论集《被背叛的遗嘱》(1993年出版)中,他讲过这样一则音乐故事。
昆德拉是在欧洲的1930年代度过少年时光的,那是犹太人的噩梦时期。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后,纳粹德国一步步蚕食别国领土,并大举迫害犹太人,犹太人被逼得纷纷失业,在被纳粹深度控制的地区,犹太人则被迫戴上那个著名的六角黄星标志。1942年左右,昆德拉父亲的一个朋友,一名钢琴老师,也成为带黄星的犹太人。父亲为了帮他一把,请他来教自己儿子,也让他能有口饭吃。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彼时早已屈服于德国的控制。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日益局促,这位老师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小钢琴经常搬家,米兰·昆德拉每次去他的新住处上课,都感觉那房间比之前又小了一点。他跟着老师学习弹奏和弦,弹奏复调练习曲,旁边都是走来走去、说着话的陌生人。房间都是与人合租的,对付一天算一天。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就这样对犹太人的集体命运有所见证。昆德拉对老师的窘迫、恐惧、朝不保夕的心情是有所感知的,至少事后是如此,而这种脆弱个体的心情,是整场巨大悲剧的一个小小写照。但昆德拉接着说,有一次下课后,老师陪他出门,走到门边时突然停住脚步,说:对了,在贝多芬的音乐里有很多乐段,非常薄弱,弱得吓人,但正因为有这些薄弱的地方,那些强有力的乐段才大放光彩。这些薄弱的地方就像……就像一块草坪,要是没有草坪,我们看到地里长出的漂亮的大树,也不会太兴奋呢。
在恐慌的气氛中,这似乎是一个短暂的沉醉和忘我。之后的故事,如果我是昆德拉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写:后来我就见不到他了,我得知,他死于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的一个主要归宿——特雷津集中营。老师对自己的结局早有预感,不过,他永远能从贝多芬的奏鸣曲里获得力量和安慰,也许他到死都是平静的,他的这种弱,正是他的强大的一部分,犹如大树周围环绕着草坪。
但昆德拉对此事仅仅做了一句简单的总结:“他不久就要去做一次残酷的旅行,然而却在一个孩子面前,高声地思索关于艺术作品的结构问题。”死于集中营,到昆德拉的笔下,成了“残酷的旅行”。他竟没有对老师的命运发表任何的哀伤,他的关注仅限于自己的幸运:“老师向我吐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关于艺术的秘密;这个思想,这个秘密,伴随了我一生。”
特雷津集中营,位于布拉格北边30英里。那个集中营在被解放后,因为发现了4000多幅被囚儿童的画作而引发震动,那些画作凝聚了天真与残忍的悲惨相遇,使特雷津在众多集中营遗址中独具“特色”。可是昆德拉避提这一令人心情压抑的故事,选择去表达一个显然更“轻”,甚至可以说更自恋的感想;他对领受了老师的金玉之言表达了荣幸,而对更“重”的事实不置一词。
我想,昆德拉那种美学至上的原则——“拒绝抒情”,或谓“反媚俗”“反浪漫”之类,从这里就能有所窥见。直截了当地表达忧郁、痛苦、悲伤,或是相反的兴高采烈、热泪盈眶,这种浪漫风格,在他眼里都是取悦观众。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命运”,是由叙事所造就,叙事则免不了要夹带情感,以取悦有可能接受这一叙事的人们。昆德拉以他眼里不揉沙子的音乐品位宣称,有必要识破这种套路,反对情感泛滥的叙事,正如有必要抵制柴可夫斯基和勃拉姆斯,此二位的音乐,对他来说正是一些包装好了之后交付给听众耳朵的悲怆和忧伤。
卡夫卡的传承
虽然如此“无情”地对待犹太老师的命运,但昆德拉的反抒情,却又实实在在与犹太人有着不解之缘。《被背叛的遗嘱》中提到最多的人物是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不仅是犹太人,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布拉格人。昆德拉曾引用他点评狄更斯的文字:
“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用这样的词句形容狄更斯的小说:‘心灵的枯燥,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卡夫卡认为狄更斯滥情:表达得很赤露,很浓烈,但人们读过后很快就会忘记。正因为内心实在枯燥乏味,所以才要极尽过分地表达。与卡夫卡同时代的流派——表现主义,也是情感恣纵的,“崇拜歇斯底里和疯狂”。表现主义在艺术领域产生了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作品,挪威的爱德华·蒙克,奥地利的克里姆特和埃贡·席勒,各有各的风格,却无不以颜料和画面表达呼之欲出的情感,或惊愕,或绝望,或痴情到变态……然而表现主义的文学作品,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几乎没有。
真要说19世纪的狄更斯在20世纪的卡夫卡面前完全过时,那倒也不尽然,至少大众读者一定会亲近狄更斯的文字,而感觉卡夫卡难以下咽。然而昆德拉热情地请读者来欣赏卡夫卡的风格,他把《城堡》《审判》《美国》这三部卡氏小说反复赏鉴。他告诉我们,卡夫卡的作品的主题是很沉重的,即“迷宫式的社会组织,人在其中迷失自己”,可是,与20世纪之前的小说家不同,卡夫卡是通过一种看起来很轻浮的途径,来把握他的主题的;卡夫卡的城堡在任何一张世界地图上都不存在,它是纯然想象出来的:
“在他的参议院叔父家里,K找到一间办公室,它像一架非常复杂的机器,有一百多个格子,服从一百多个按钮的命令,一件既实际而又完全无用的杂物,既是技术的奇迹,同时又无意义。在这本小说里,我数了数有十个这种绝妙的机关,好玩,而且古怪,从叔父的办公间,乡村的迷宫式的房子,‘西方’酒店(建筑复杂得可怕,组织极其官僚),到俄克拉荷马剧院,它也是个无法弄懂的行政机关。”
卡夫卡在1924年,40岁出头就病逝了。他的死后盛名首先归功于那份“被背叛的遗嘱”——马克斯·布罗德没有遵其遗嘱销毁他的作品,反将其出版和传播;其次归功于瓦尔特·本雅明、赫尔曼·布洛赫等人对他的价值的发现;再然后,昆德拉又为此加了一把大力。他说,卡夫卡的写作才是真正的诗意创造,创造出了一个“极为无诗意的世界的极为诗意的形象”。这话具有无私的悖论力量,很可能迫使信任他的读者再次拿起一本《城堡》《审判》或《美国》,去努力咀嚼那实在不太可口的文字。
归根结蒂,卡夫卡(基于他自己的人生体验)设法描述的,是一个官僚化的、文牍主义的现代社会,它本身极为无聊,带给人的主要体验也是麻木,是无可奈何。它是一种真空,从卡夫卡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它都没有任何本质性改变(参考一个统计数据:“美国人一生得花6个月的时间填表”)。卡夫卡通过他的K来直面官僚制的循环、空洞,描述它那蠢不可及的程序,它对人的生命的无情浪费,但小说本身也必须像迷宫一样使人麻木、烦躁,乃至卡夫卡自己都深陷其中,至死都不能确信写出了能够传世的作品。
昆德拉是最看重幽默与“笑”的,他将卡夫卡的小说阐释为诗意的、只有现代社会才能造就的喜剧,然而他只能用异常严肃的语气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欣赏这种喜剧,以及,欣赏这种喜剧有多么难。他说:卡夫卡的《美国》使“我们处在一个感情不适时宜、错置时宜、过分夸张、不可理解,或者诡异地不存在的世界”;他还说,卡夫卡把《审判》的第一章念给朋友听的时候,人们都笑了,而读者只有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才会在读《审判》的时候强迫自己去笑。
向媚俗宣战
幽默最难理解。向人们分享一个悲剧故事很容易,而要分享一个幽默就要难得多。当读者或观众问起“笑点在哪里?”的时候,你再加以解释都是很无力的。然而,幽默又是反抒情、反浪漫的必备利器。昆德拉从来不吝赞美拉伯雷的《巨人传》、斯特恩的《项狄传》以及狄德罗的《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他认为,这种风格怪诞、情节夸张的小说,是想象力得到真正施展的时刻,可是,读者要想沉浸在这些书的“魔法所创造的世界中,任自己被异想天开和极端所挟去”,可比被巴尔扎克、狄更斯、左拉等人的小说中浓郁的情感所打动的难度要大得多。
也正因此,昆德拉不得不一次次向那个捷克幽默求助:
——太太,一个压路滚筒从您的女儿身上压过去了!
——那好,那好,我正在我的浴缸里,把她从我的门底下塞过来,把她从我的门底下塞过来吧。
“应不应该控诉它的残酷?”昆德拉问。如果控诉了,或者至少感到心里不舒服,那么你的感受力就只能处在一种低档的、流俗的档次之上,就只能被抒情的诱导牵着鼻子走。非得凭着一种不认真的玩笑精神,你才能从抒情化的桎梏中摆脱出来。
昆德拉一生写了三本文论,《被背叛的遗嘱》之前还有《小说的艺术》,此书中收入了他在1975年去以色列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演讲。正是在这篇讲辞中,他集中说出了几个重要的美学观点,其中之一就是反媚俗。昆德拉将这个思想归功于赫尔曼·布洛赫,他说:
“媚俗一词指一种人的态度,他不惜一切代价取悦大多数人。为了使人高兴,就要确认所有人想听到的,并服务于既有的思想。媚俗,是把既有的思想用美与激动的语言翻译出来,它使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思索的、我们感觉的平庸留下同情的眼泪。五十年后的今天,布洛赫的话具有更真实的意义。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取悦人,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变成媚俗的美学……”
反媚俗的观点,将反抒情、反浪漫等提法都吸收在内。它非常尖锐,但又绝对孤高,它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是非主流的一方,也是铁定要失败的一方。布洛赫也是犹太人,但和布拉格的卡夫卡不一样,生活在维也纳的布洛赫(1938年52岁后流亡美国)一直以才华自恃,当他在1931年出版《梦游人》的时候,他要求出版商在推介文中将他和詹姆斯·乔伊斯以及安德烈·纪德并提。昆德拉将自己放在了布洛赫这一脉之中,毫无保留地向他眼里被大众传媒所主宰的现代审美宣战。
世界公民的梦想
讲辞中另一个观点,就是著名的“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是一句犹太格言,实际上也是最早将“笑”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格言。昆德拉将其中的张力阐释了出来:“因为人越是思索,真理就躲开了他;人越是思索,这个人与那个人的思想就相距越远。”进入现代的过程,是一个真理丧失了唯一性的过程,《巨人传》《项狄传》《定命论者雅克》以及《堂吉诃德》,都抓住了“人的这一新的境况,并在它之上建立了新的艺术,即小说的艺术”,能够欣赏这种艺术的人将成为快活的人,否则就是不快活的人,他们听不到上帝的笑声。
快活就意味着自我的解放,而不快活的人,依然坚信真理是明白的,所有人都应该思考同样的东西。站在耶路撒冷的讲台上,昆德拉将他的这个洞察,归功于对“犹太世界主义”的感激,具体而言,就是卡夫卡和布洛赫,这两位中欧出产的犹太作家的创作所孕育的精神。犹太人是特殊的,他们既然被从自己的起源地放逐出去,也就得到了一个凌驾于“种种民族主义热情”之上、抵达世界主义的天赐良机,犹太世界里的伟人,总在热切畅想一个超民族的、文化的欧洲。接下来,一生都很少表露政治观点的昆德拉,向以色列送上了一句力道千钧的嘱托:
“欧洲十分可悲地背叛了犹太人,但是,假如犹太人仍能保持对欧洲世界主义的忠诚,那么我想说,以色列,这个犹太人终于重获的小小家园,是欧洲真正的心脏——一颗位于身体之外的特别的心脏。”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整个欧洲都屈服于纳粹德国的压力,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犹太人。这就是“欧洲的背叛”,它当初导致了昆德拉的音乐老师落入“一段残酷的旅程”,殒命特雷津。但散居各国的犹太人遭遇的厄运,可以解释为一种天然的世界主义被民族主义的狂热野心所扼杀。1929年出生于捷克的昆德拉,希望这种世界主义能够继续由犹太人所保留,特别是,如果卡夫卡和布洛赫代表的现代主义美学能产生持久的生命力,那么,这也可算是昆德拉所在的“中欧”的荣耀。
但也就是在1975年,他也离开布拉格,移居去了法国。他获得了法国国籍,却选择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不再公开发言,绝少接受采访。在耶路撒冷的这番演讲,最高级、最精彩之处,在于昆德拉从卡夫卡那里吸收的犹太式的悖论思想:位于身体之外的心脏是真正的心脏;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的“家”,一片弹丸之地,却凝缩和容纳了一个巨大的做世界公民的梦想。在这样讲的时候,昆德拉已经将自己投入了进去。他也是这梦想的承载者,不再有祖国,生活在一个孤悬于流俗之上的审美的高度。

《小说的艺术》
米兰·昆德拉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4月版

《被背叛的遗嘱》
米兰·昆德拉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9月版
判处无期徒刑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李杰翔受贿案一审宣判
对李杰翔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2024年2月27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青海省委原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李杰翔受贿一案,对被告人李杰翔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李杰翔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0000江苏武进一企业因粉尘爆炸致8死8伤
事故现场救援已结束,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开展中。记者20日从常州市武进区应急管理局获悉,1月20日3时38分,位于武进区南夏墅街道的常州燊荣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粉尘爆炸,共造成8人死亡、8人轻伤。事故现场救援已结束,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开展中。0000“榴莲贵”频上热搜,平台销量增七倍,是谁推高了价格?
即使今年我国榴莲的进口量增大,还是抵不住直播带货、话题发酵导致的供不应求。“榴莲盲盒”成了今年夏天的新名词。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一起开榴莲盲盒”、“榴莲盲盒开箱”、“快乐就是开榴莲”、“今天的快乐是榴莲给的”成为了热议话题。由于外形大小、重量相似的榴莲,果肉的数量(单位为“房”)和大小差别极大,甚至有网友调侃:“当代三大合法赌博:烫头、结婚、买榴莲。”锤子财富2023-05-26 20:13:010003资管巨头警告:政府停摆将让美联储暂停加息,但这个问题更危险
标普500指数或下跌15%。美国经济如今正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政府因为资金即将耗尽陷入停摆近在眼前,而能源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影响也让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变得扑朔迷离。资管巨头Pimco19日发布报告表示,美国政府可能在月底全面停摆,使美联储不愿在11月加息,但油价走高等威胁因素则可能导致标普500指数近期下跌15%。停摆料冲击经济锤子财富2023-09-20 15:42:400000中央汇金:已于近日扩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增持范围
中央汇金公司充分认可当前A股市场配置价值,已于近日扩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增持范围,并将持续加大增持力度、扩大增持规模。2月6日,中央汇金发布公告,中央汇金公司充分认可当前A股市场配置价值,已于近日扩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增持范围,并将持续加大增持力度、扩大增持规模,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锤子财富2024-02-06 10:12:370000